导语:仅仅完善欧元治理框架并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欧元的存在性危机。从长期来看,欧元的信用水平取决于区域内整体经济发展情况。只有通过提高区域内劳动生产率增速,纠正经济结构性失衡,才能实现共享的繁荣,使民众的生活水平得以持续改善和提升。也只有建立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基础上的长期经济发展才能切实增强欧元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才能给欧元一个稳定的未来。
【摘 要】欧元作为世界第二大货币,欧元区的经济发展和凝聚力是其货币实力的主要支撑。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后,欧债危机引发的希腊退欧风险对欧洲货币联盟的基础造成冲击,进而引发欧元的存在性危机和治理框架危机。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及难民危机背景下不断高涨的反全球化和反一体化民粹主义浪潮,再次拷问欧元的长期前景。表面上看,目前关于欧元命运的担忧源于政治冲击,实际上问题根源仍然在经济层面。欧元区多数成员国的中下层民众生活水平无法得到改善,既源于欧债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更源于欧元区内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停滞和国家间劳动生产率的分化。欧元治理框架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欧元的信用水平,但要从根本上解决欧元的存在性危机,关键还在于能否提高区域内劳动生产率增速,纠正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并实现繁荣共享。
【关键词】欧元危机 政治冲击 劳动生产率 区域失衡
The Nature and Prospect of the Euro Crisis and the Role of Labor Productivity
Abstract: A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currencies ,the status of euro is determined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urozone as a whole as well as its cohesion. In 2009 the euro debt crisis posed a threat to the foundation of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then trigged the crisis of euro collapse. The United Kingdom voted to leave the European Union in 2016, the trend of anti-globalization and anti-integration caused reflection on the future of the euro. The primary cause of the instability stemmed from economic problems although it seemed that political shocks affected the fate of the euro. Slower world growth from financial crisis after 2008, the slowdown in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the widening productivity gap among members of the eurozone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unimproved living standards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classes in most eurozone members. Although the credit of euro can be improved to a certain extent through reforming governance structure, improving productivity growth to resolve the unbalance among eurozone members and realizing shared prosperity should be the core element to solve the existence crisis of euro.
1999年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成立是世界经济史和货币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但从启动阶段开始,关于欧元的政治上的考虑就迫使经济问题退居其后,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结构缺陷和基础脆弱性[2],并为日后货币联盟体制遭受冲击,甚至危及欧元的存在性,埋下了隐患。
欧元区成立的前十年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9-2008年欧元区国家经济取得了平均2.1%的实际增长率,略小于美国的2.6%,欧元也成为仅次于美元的世界第二大交易和储备货币。尽管在这十年里也曾有过各种摩擦,但都淹没在经济繁荣的大潮里。直到2009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并蔓延至欧元区其他国家,打破了长久以来的平静。从此欧元区开始遭遇频繁的内外部冲击,欧元区的结构性缺陷日益暴露甚至被放大,关于欧元的命运也引起了各界的争议。虽然人们对导致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本性原因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大家普遍认为通过体制改革和完善,欧元将可以突破眼前的困境,并获得更好的发展。就像“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所坚信的,“通过适当的措施可以不断地巩固和完善欧元区,欧元区的问题并不是欧元本身的问题,除非欧洲发生政治变革,欧元绝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3]。
欧元作为一种货币,其在降低欧元区国家之间的交易成本,促进区域内贸易方面充分发挥了积极作用。令欧元饱受诟病的是,它作为一种宏观货币政策工具,不能兼顾经济发展显著差异的所有成员国的需求。但实际上,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欧元体制天生具有的缺陷并不比主权货币情况下糟糕多少。即使是在货币和财政政策都统一的主权国家,货币政策在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调整结构失衡方面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只因为欧元区是一种主权国家联合体,那些失去宏观货币政策工具的成员国对欧元的怨气更大而已。问题的关键是,欧元区在面对债务危机、经济停滞和宏观政策工具捉襟见肘的同时,区域政治危机正使得欧元问题雪上加霜。
目前看,2016年欧洲地区愈演愈烈的政治危机并没有很快被扭转的趋势。2017年德国大选、法国大选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意大利甚至已经被警告有可能退出欧元区[4]。作为欧元区前三大经济体,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态度和动向毫无疑问对欧元的命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实际上,这次人们对欧元命运的普遍忧虑始于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英国公投之后,欧元区民众疑欧、反欧的情绪愈演愈烈,欧洲政治危机对欧元区的冲击引发人们对欧元深层次问题的反思。2016年8月份,斯蒂格利茨撰文指出,欧元区的结构、指引和构建欧元区的规则和制度存在更为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无法克服的,因此引出了一种前景——是时候更全面地反思欧元了,甚至可以考虑放弃欧元了[5]。尽管我们的相关研究并不完全支持斯蒂格利茨所谓的欧元区制度缺陷根本原因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欧元区当前所面临的政治冲击确实非常严峻,欧元的前景始终笼罩在各种危机的阴影下。对于欧元区能否渡过2017年的政治冲击,并在制度基础和其他更深层原因方面找到对策,增强人们对欧元的信心,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目前欧元区面临的问题,表象上是反全球化和地区民粹主义等政治问题,深层次的原因依然是经济问题。我们后面的研究将证明,从根本上看,欧元区的问题主要还是劳动生产率增长停滞和区域劳动生产率增长分化的问题。
围绕这一问题,后文将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欧元危机的内涵、性质及原因(文献回顾);2016年以来欧元危机的新特点;欧元区劳动生产率分化及其对欧元的影响;造成欧元区劳动生产率停滞和区域分化的原因。最后是简要结论与思考。
一、 欧元危机的内涵、性质及原因:文献回顾
“欧元危机”(Euro Crisis)的说法,最早在2010年上半年见诸中外媒体,2010年下半年出现在学术期刊中。但迄今为止,在大多数文献中,“欧元危机”(Euro Crisis)与“欧元区危机”(The Euro Area Crisis)、“欧债危机”(European debt crisis)仍然是混用的[6],甚至很多文献并未给出欧元危机的确切含义。那么,欧元危机的确切内涵到底是什么?
从语意本身理解,既然和美元、日元、人民币等货币一样,欧元同样是一种执行着交换媒介、价值尺度、储藏手段和支付手段等职能的可交易货币,那么,欧元危机就应当是一种货币危机,在表现上,则应当呈现为欧元信用危机和银行支付危机。但实际上,无论是国内文献,还是西方学者的研究,从货币信用危机角度来讨论欧元危机的文献并不多[7]。
国内学术界关于欧元危机的讨论从2010年5月份见诸报章杂志。初始阶段,这些声称发生了“欧元危机”的文章,其主要证据或者是穆迪等机构的主权信用评级,或者是欧元在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上半年对美元较大幅度贬值,或者是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5月共同推出的7500亿欧元救助计划[8],甚至一些文献干脆假定欧元危机是先验事实[9]。在这些国内学者关于欧元危机的研究中,基本没有关于欧元危机的内涵和性质的明确界定和说明。其中,仅有赵柯在“德国的‘欧元保卫战’:国际货币权利的维护与扩张”一文中,探讨了欧元的存在性问题,接近于把“欧元危机”定性为“欧元存在性危机”[10]。
西方学术界关于欧元危机的研究在2011年之后逐渐增多,2012-2014年是是文献发表的高峰,之后逐渐减少,但研究转向深入。但如前所述,很多以“The Euro Crisis”为题的研究,其实际内容是关于“欧元区危机”(The Euro Area Crisis)、“欧债危机”(European debt crisis)的探讨[11]。之所以出现这种名实不符的情况,是因为,在绝大多数学者看来,尽管欧元危机首先是一个问题银行的债务偿付能力危机,进而影响到欧元信用,并引发欧元汇率在2010年10月至2011年6月出现较大幅度波动,但“总的来说,欧洲货币联盟项目的货币支柱运作良好,因此说它是一个‘欧元’危机是不正确的,虽然它是当前危机的中心。”[12]即使从引发欧元危机的希腊、葡萄牙等国的债务危机角度看,也可以发现,“欧洲发生的危机与其说是债务危机,毋宁说是政治机会主义危机。”[13]
梳理2011年以来关于欧元危机的学术文献,可以发现,对欧元危机的研究主要是在以下几个维度和内涵上展开的:
(1)欧债危机意义上的欧元危机。德国学者霍尔(Hall, 2012)认为,“过去三年,困扰欧洲的欧元危机,是指为解决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GIIPS)面临的债务问题而进行的斗争,它不是要打破货币联盟或在欧洲引发更广泛的金融危机。”[14]
(2)货币危机和信用危机意义上的欧元危机。但这种货币危机的约束条件和出路却是政治性的。弗莱登(J. Frieden,M. Copelovitch,S. Walter)等在“欧元危机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指出,“经济学家们对欧元危机的原因有越来越多的共识:危机是一种经典的国际收支危机,向欧元区国家的资本流入‘突然停止’,引发经常账户赤字……。由于缺乏最后贷款人,危机加剧了,进而引发欧元贬值和经济危机反应”。“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欧元危机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包括欧元区劳动力缺乏流动性,欧元面临非对称冲击的脆弱性以及缺乏足够的财政稳定,都是造成欧元危机的重要原因。但将重点放在确保欧元区生存所必需的财政或银行联盟的最佳设计上,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欧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项目,政治目的甚至超过了经济目的。因此,欧元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政治危机,欧盟面临的政治制约对欧元危机及其解决影响更大。”[15]
(2)治理结构危机和政治危机意义上的欧元危机。在这个意义上,欧元危机已经影响到欧元本身在未来的存在性问题。
这个方面的文献是最多的。比如,埃德蒙·阿尔范德瑞(Edmond Alphandéry)指出,欧元危机本质上是“欧元区财政纪律问题”,“加强欧元区的多边监督,更加有效地执行财政契约条款,提高欧元区的治理水平,仍然可以维护欧元作为单一货币的基础。”[16]
维李特和斯瑞森(TD. Willett,N. Srisorn)分析认为,“在创造欧元时,它们没有认识到货币一体化与贸易一体化有根本的不同,欧元国家集团整体上没有达到最佳货币区域的标准。此外,为欧元创造的机构基础设施太脆弱,无法应对新出现的问题,一旦爆发,就无法有效应对危机。”[17]
海斯(A. Heise)则直接从治理结构的角度指出,欧元危机本质上是欧元的“治理框架危机”,“目前这种‘没有政府的治理’是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这种治理结构无法满足欧元区货币稳定和经济稳定的需要。要避免欧元区的分裂,一种基于后凯恩斯主义原则的‘政府治理’是必须的。”[18]
比拉门迪和斯蒂格穆勒(P. Beramendi,D. Stegmueller)从欧元区成员国面临的民族主义和政治动荡角度出发,认为目前的欧元危机在本质上是欧元区的“政治危机”。“统一货币条件下,欧元区发生了财政和福利再分配的重大转移,但欧盟领导人并没有致力于欧元区的财政一体化,或者通过财政转移来解决欧元面临的财政风险。背后的决定因素是由欧元区的政治地理及其不同区域的选民偏好。”[19]。
政治危机和治理危机的严重性在于,无论是作为货币危机,还是作为治理结构或政治危机,“欧元危机都正在对欧洲货币联盟的存在构成挑战,这是问题的关键。”[20]
(4)结构性竞争力危机意义上的欧元危机。丹尼尔·罗德里克从纯经济理论的角度指出,“欧元危机在本质上仍然是经济系统的高债务和低竞争力危机”。他转述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哥夫(Kenneth Rogoff)的话指出,“解决欧元区危机的唯一可行策略是大幅度减记那些外围国家的债务,这对德国和法国而言的确很难,但他们必须认识到这些钱已经失去了,假装仍然拥有这笔债权的游戏不可能无限期持续下去。”[21]
(5)一种综合性的观点认为,“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期,欧元危机首先是一个问题银行偿付能力,然后是主权债务问题,继而则是完整的欧元区及其货币的稳定问题。……欧元危机不仅仅是金融危机,也是一场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危机。”[22]
借鉴已有的文献,结合欧元区2010年以来的金融、经济和政治状况,可以发现,从内涵和性质上看,与主权国家的货币危机不同,欧元危机具有货币危机、欧元存在性危机和欧元治理框架危机的多种性质和综合特征。
那么,欧元危机为什么会表现出这些综合特征?直观地看,首先是因为,欧元作为一种信用货币,与主权货币一样,具有交换媒介、价值尺度、储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等职能,因此,欧元危机也必然同样具有货币危机的一般特征;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作为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体化的标志性成果,欧元是一种主权国家联合体的共同货币。在这个意义上,欧元危机一方面将表现为欧洲货币联盟的基础是否稳固的问题,另一方面表现为欧元作为区域货币的存在性问题;最后,欧元作为一种非主权货币,其治理框架和治理结构与主权货币有很大差异。因此,欧元危机还会表现为欧元的治理结构危机。2016年以来欧元危机表现出的新特征进一步凸显了欧元危机的这些性质。
二、2016年以来欧元危机新特点
如前所述,作为主权国家联合体的单一货币,2009年的欧元危机首先是银行支付能力问题,进而则是希腊债务危机引发退欧风险可能引发的欧洲货币联盟基础和欧元存在性问题,以及欧元治理框架的调整和改革问题。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并于2017年3月29日正式启动了脱欧程序,这进一步动摇了欧元的政治基础。尽管2017年3月16日荷兰极右翼自由党在大选中落败,但是即将到来的法国总统大选中极左派和极右派当选的可能性在增加,两位候选人都带有明显的“反欧”属性。已经拉开序幕的德国大选和被迫提前的意大利大选中右翼民粹主义走上前台使得欧元危机的政治性越来越突出。
1.2016年以来欧元区的政治危机愈演愈烈,成为欧元面临的主要冲击
2009年由希腊开始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使得欧元区经济整体陷入衰退,部分国家至今仍未能走出衰退的阴影,欧元与美元的汇率由2009年12月的1.44下降到2016年12月的1.06,贬值26.39%。如今,欧元很有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政治冲击。2016年6月23日英国公投脱欧,2016年12月4日意大利公投修宪失败,2017年已经拉开序幕的法国总统、德国总理大选以及被迫提前的意大利大选的不确定性都为欧元的未来蒙上了阴影。
虽然同样是关于欧元的存在性危机,与2009年源于外围国家的经济冲击不同,本次危机主要源于核心国家的政治冲击。如果说欧债危机的主角是政府和市场,那么当前欧元面临的政治危机的主角则是沉寂已久的公民。这表明大多数的欧洲选民并没有对欧元交口称赞,相反,人们认为欧元带来了很多问题。单一货币、统一市场、技术进步固然带来诸多红利,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从中获利,精英阶层成为最大的赢家,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从基尼系数看,自2005年以来,欧元区整体基尼系数呈上升趋势,德国、法国、西班牙等的上升幅度都超过了欧元区平均水平。截止2015年,欧元区大部分国家的人均GDP尚未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民众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得到持续改善,反而有所下降。反全球化、反一体化、反精英都是民众对收入差距扩大、财富和资源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全球化与技术变革加速导致底层阶级甚至部分中产阶级对谋生能力丧失的担忧,是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下利益受损的公民试图寻找改变现状的一种选择。从英国脱欧的公投结果中可以发现,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比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更倾向于留在欧盟,国际化程度高、相对富裕的地方普遍支持留欧,而以农业经济、传统工业为主的地方则更加倾向于脱欧,这些地方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制造业转移,失业增加,收入减少,成为全球化的利益受损者[23]。
2.政治危机伴随政策空间收缩使得欧元存在性危机风险大幅度上升
就欧元的经济基础来看,2016年欧元区国家普遍面临“生产率增速下降、债务水平提高、货币政策效果减弱”的风险三角的冲击。实际上,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风险三角”普遍存在[24],欧元区也不例外。但由于欧债危机的影响以及欧元区特殊的结构、机制和规则问题,其化解风险三角的难度更大。
根据OECD的统计,2007-2015年欧元区以劳动者单位产出衡量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为0.4%,远低于危机之前2000-2006年的0.9%,也低于同期欧盟的0.5%,美国的1.0%。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则由1999-2006年的0.1%降低到2007-2013年的-0.7%。生产率增速的下降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复苏进程和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25]。2015年,欧元区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GDP仍低于2007年的水平,而美国、欧盟、OECD等均已超过危机前水平。欧债危机后,尽管欧盟委员会和欧洲中央银行要求重债国紧缩财政降低政府赤字,但是欧元区的政府债务水平不降反升。2011年欧元区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为87.0%,2015年上升到93.3%。重债国希腊则由172.0%上升到177.4%,其他国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债务水平增加,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债务水平都超过了《马斯特里赫条约》规定的60%标准[26]。尽管欧洲央行通过多轮量化宽松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但是欧元区整体通货膨胀率仍然保持在极低的水平,2015年通货膨胀率为0.0%,预计2016年为0.21%,部分国家尤其是当年的重债国希腊、爱尔兰等仍处于严重的通货紧缩状态[27]。劳动生产率增长停滞,经济增长缺乏核心动力,名义GDP增长缓慢甚至下降,政府税收收入减少,通货紧缩又使得利息负担加重,其结果是,即使在没有新增债务的情况下,政府债务负担也逐渐增加。
为了缓解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应对通货紧缩,刺激经济增长,欧洲中央银行甚至将隔夜存款利率下调至零以下,但是这种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未能将欧元区经济拉出通货紧缩的困境。一方面,由于全球储蓄过剩和投资意愿的缺乏,货币政策效果不断减弱;另一方面,由于资产负债表效应,银行审核贷款时更加审慎,造成实际上的信贷收缩,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传导到实体经济。不仅货币政策效果减弱,危机后在政府债务水平已经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空间也很有限。首先,债务水平已经很高的国家必须付出更高的成本从市场融资,若产生的收益不足以覆盖融资成本,政府债务将进一步恶化,当不能继续从金融市场融资时就会面临政府破产的风险;其次,政府投资也逃不开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也会不断减弱;第三,危机爆发后,接受援助的国家在获得资金支持的同时也必须接受资金提供方的条件,包括实施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削减开支、增加税收、推进经济结构改革。这种紧缩性的安排可能会加深经济衰退程度,进一步推高政府债务水平。再加上美元进入加息周期,资本将大量流入美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将处于两难境地,给欧元区的经济恢复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以来,欧元面临的政治风险冲击和“风险三角”冲击,是欧元危机的新特征。目前来看,政治风险冲击的不确定性短期内无法消除。这一方面是因为,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世界经济环境不利于欧元区经济恢复,从而也不能为消除区域内政治冲击提供有利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欧洲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的影响使得努力维系欧盟稳定的默克尔政府面临政治考验,作为欧盟三驾马车的法国大选和意大利国内政治走向也不利于欧盟的稳定。与此同时,面前欧盟经济的基本面还无法解决“风险三角”的冲击。
从欧元的存在性和治理框架危机产生的根源看,“风险三角”中的劳动生产率因素更具致命性。因为不存在权力协调问题,因此,相对于欧盟,单一主权国家的政府债务问题和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更容易解决。欧元区则不然。欧元区成员国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宏观货币政策这一干预经济的工具,同时,债务规模和债务结构又受制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限制,这使得“风险三角”中的生产率冲击更具致命性。
那么,从逻辑机制看,欧元区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是如何影响欧元的呢?我们先从欧元区共同货币条件下区域内劳动生产率的分化入手,来逐步展开下面的分析。
三、欧元区劳动生产率分化及其对欧元的影响
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都表明,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它决定着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长期经济效率和竞争力。单纯依赖增加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和低效的,因为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要素投入的增加,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最终将使增量投资的增长效应降为零。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劳动生产率增速普遍下降的趋势下,欧元区也没能例外。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期望通过要素充分流动实现资源在区域内的合理配置,提高区域内整体劳动生产率,从而提升经济增长效率,这是一体化发展的主要经济动机。但这被证明过于理想化了。不仅欧元区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增速随世界经济形势波动,而且,区域内各国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不仅没有因为加入欧元区而缩小,甚至有扩大的迹象。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既没有体现出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独特优势,也没有缓解各经济体之间的发展失衡,从而引发民众的广泛质疑和排斥,其竞争力和凝聚力也受到极大削弱。
1、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欧元区整体经济疲软
按照理想的路径,欧元诞生后,单一货币应当有利于稳定价格、降低通货膨胀率,加速欧元区内部生产要素的流动,优化要素配置提高整体劳动生产率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但是,从数据来看,到目前为止欧元区并没有因为其单一货币,单一市场获得独特的发展优势,其与美国和欧盟在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趋势上基本一致。图1描述了部分主要经济体2001-2015年的GDP增长趋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趋势。
从图1(a)和图1(b)可以看出,各主要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在劳动生产率增速较快的时间里,经济增长的速度也相对较快。尽管趋势上保持一致,但是在波动幅度和波动持续时间上,各主要经济体之间差别显著,欧元区的波动幅度和波动持续时间都远远超过美国。图1(b)显示,自欧元正式流通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欧元区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不仅低于美国,而且低于欧盟,欧债危机爆发后其劳动生产率增速急剧下滑,2009年时甚至下降到了-2.7%,远远超过次贷危机时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降程度。劳动生产率的急剧波动必然伴随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因此,当美国走出危机的影响并恢复稳定增长时欧元区经济仍然疲软就不足为奇了。若欧元区的劳动生产率不能得到有效提高,经济持续疲软,加上政治不确定因素的增加,欧元的竞争力将受到极大削弱,其前景也将越来越不明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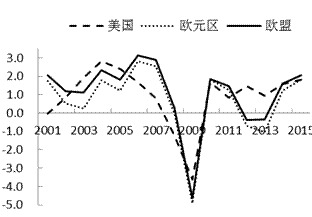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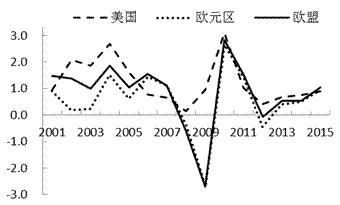
图1(a):部分主要经济体人均GDP增长率[28] 图1(b):部分主要经济体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数据来源:http://data.worldbank.org/; 数据来源:https://data.oecd.org/
2、劳动生产率差异加剧欧元区内经济结构性失衡
根据Balassa-Samuelson(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将国民经济划分为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时,各国不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远小于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因此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是影响实际汇率的关键原因。即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高于另一个国家,则该国的货币将升值[29]。但是,在欧元区单一货币的情况下,这种汇率调整不可能实现。欧元汇率无法对区域内生产率冲击做出及时调整,这意味着,欧元区内劳动生产率增速相对较快国家,实际上相当于面对货币贬值。这强化了该成员国的竞争优势,使得经常账户改善或者盈余进一步积累。对于劳动生产率增速较慢的国家而言,叠加隐形的实际货币升值,进一步削弱其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导致经常账户恶化或者逆差进一步扩大。因此,在丧失汇率调整工具的情况下,欧元区内缓解发展失衡的关键是缩小劳动生产率差距,只有各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保持大致相当的速度,实际汇率扭曲的影响才得以缓解。
图2(a)和图2(b)显示了欧元区主要经济体在危机前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和经常账户的变化情况。相比危机之前,主要经济体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差异有所缩小,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由危机前的3.3%、0.9%和1.7%上升到危机后的4.3%、3.0%和2.3%,而作为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的法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则从3.3%下降到2.9%。不管是危机前还是危机后,德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始终保持较高的增速,这是其制造业竞争力得以保持和不断发展的关键因素。一方面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使其经济效率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相对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使其获得实质上货币贬值的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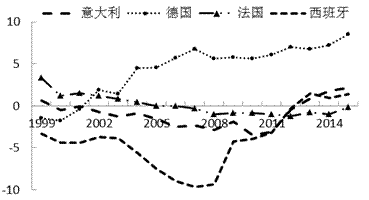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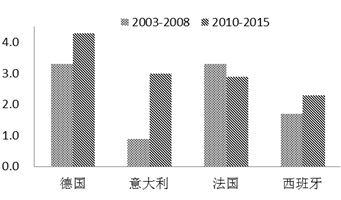
图2(a):欧元区部门国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变化情况 图2(b):欧元区部门国家经常账户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 数据来源:http://data.worldbank.org/
从图中还可以看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与各国经常账户的变化息息相关。德国自2002年实现贸易盈余以来,贸易顺差不断扩大,2015年其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重达到8.5%。尽管西班牙是欧债危机的发源地之一,2007年其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重高达9.68%,但是危机后该国政府实施的一系列结构改革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极大地提升了西班牙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国际贸易失衡状态得以改善,2013年甚至开始实现经常账户盈余。法国的表现则相对较差,危机后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导致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不断丧失,直到2013年意大利基本上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时,法国仍处于逆差状态。
四、造成欧元区劳动生产率停滞和区域分化的深层次原因
欧元区劳动生产率发展不平衡既体现在欧元区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停滞,又体现在欧元区内部各成员国之间劳动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除了各成员国在加入欧元区时即存在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以外,全球总需求不足,成员国产业结构调整缓慢,资本错配,以及欧元体制本身,都对加剧欧元区劳动生产率发展失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总需求不足
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增长中枢不断下移,总需求不足日益成为困扰全球经济复苏的严重问题。2012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未再超过3%,预计2016年的实际增长率亦不会超过3%,远远低于3.75%的长期平均增长率。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增长率持续处于低位,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大幅回落的趋势难以遏制。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0-2015年美国和日本的平均实际增长率分别为2.2%和1.3%,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速分别由2010年的10.6%和10.2%下降到2015年的6.9%和7.5%[30]。预计2016年将进一步减速,世界经济复苏之路困难重重。为遏制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复苏,各国纷纷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部分国家/地区甚至进入负利率时代,但是全球通货膨胀率仍在低位运行,反映了消费需求的疲软。2015年全球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增长率为2.37%,远低于2007年的4.03%,尽管近几年美国消费需求增速明显,但是消费支出在GDP中的比重并无明显改善。实行负利率的日本和欧元区2015年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0.8%和0.0%,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增长率分别为-1.2%和1.84%,仍有随时滑向通货紧缩的风险。发达经济体增长点的缺乏,新兴经济体过剩的产能使得全球投资收益率处于低水平,货币的大量发行和实际利率的不断降低并没有能够刺激投资需求,2010年以来全球总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持续下降,到2015年该增长率已经下降为2.85%,相比2007年的5.76%下降超过50%[31]。企业普遍较低的投资意愿,造成人均资本存量下降,在无新技术冲击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增速也必然下滑。疲软的内外部总需求不利于欧元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发展失衡状态的改善。
2、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
鲍莫尔-福克斯假说认为,与工业和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生产率增长滞后,如果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过快增长,将导致总体经济生产率增速的下降[32]。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服务业在欧元区经济体中比重过大且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2年的70.6%上升到2015年的74%,希腊的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80%,同期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27.2%下降到2015年的24.5%[33],即使在危机后,这一变化趋势也未能得到有效遏制。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反映了欧元区普遍存在的过早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缺乏结构性基础,难以持续。
尽管欧元区各国工业比重都比较低,即使是德国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也只保持在30%左右,但是各国在工业内部细分产业结构上存在巨大的差别。德国始终坚持发展制造业并以高技术含量的机器和运输设备、化工产业等作为其支柱产业,通过持续的产业升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保持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2015年德国机器和运输设备、化工产业的增加值之和占其制造业增加值的一半以上,高技术产品出口是法国和意大利之和的1.5倍[34],坚实的工业基础使其能够在危机后迅速摆脱负面冲击的影响并恢复增长。外围国家如葡萄牙的制造业则以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技术含量低加上较高的劳动力成本使其在国际竞争中更易受到不利冲击的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更加困难。
3、资本错配
(1)资本在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错配
如果将一国生产部门划分为贸易部分和非贸易部门,则贸易部门相对非贸易部门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更高,各国非贸易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小于贸易部门,而且非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总是小于贸易部门。因此,各国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主要在于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非贸易部门的非理性繁荣反而会降低一国的劳动生产率[35]。首先,非贸易部门的过度繁荣将挤占用于贸易部门发展的资本,造成贸易部门资本存量的降低,生产率下降;其次,由于非贸易部门是相对劳动密集型的,其过度发展必然引起全社会工资水平的提高,贸易部门的生产成本随之上升,投资回报率下降,新增投资减少,生产率下降。
欧债危机爆发之前,爱尔兰、西班牙和希腊的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流入,由于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多年经济增长中积累的资本未被用来继续支持高生产率的制造业发展,而是流向了低生产率的房地产市场。根据OECD的统计,2000-2005年爱尔兰、西班牙和希腊的住宅类固定资产投资占总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分别由34.1%、33.5%和36.4%上升到43.7%、38.9%和42.2%。[36]这种资本过多向非贸易部门的低效甚至无效配置必然使得劳动生产率的下降。2000-2005年爱尔兰的劳动生产率增速由5.2%下降到0.8%,同期,西班牙由0.3%下降到-0.5%,希腊由3.6%下降到-0.3%。虽然危机后,住宅类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降,但是由于非贸易部门的繁荣造成的贸易部门萎缩难以在短时间内得以扭转,使得改善劳动生产率发展失衡的政策难度加大。
(2)资本在不同效率企业之间的错配
经济活动中企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资本在不同劳动生产率企业之间的配置将影响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Gamberoni, E., C. Giordano and P. Lopez-Garcia对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研究发现,2002-2012年除德国以外其他国家的资本更多地流向了低生产效率的企业[37]。
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错配,从形成机制上看,与单一货币体制下不同国家的金融深化程度有关。在分析葡萄牙债务危机的形成原因及其冲击时,里卡多·赖斯(Ricardo Reis)建立了一个信用摩擦模型,用来证明,在单一货币区内,“如果成员国的金融一体化程度超过金融深化,非贸易部门将以牺牲劳动生产率更高的贸易部门为代价,出现萧条性扩张,则该国的整体生产率将下降。”[38]这一逻辑运用到欧元区内那些金融深化率相对落后的希腊等其他南欧国家时同样适用。
4、欧元体制约束制约劳动生产率不平衡的调整
欧元作为一种非主权货币,欧元区也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其成立时各成员国并不满足趋同标准,因此,在统一的名义汇率和名义利率下,各国面临的实际汇率和实际利率并不相同。货币政策工具的丧失和替代工具的缺乏加重了低劳动生产率国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难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劳动生产率的失衡。
在加入欧元区时,各国劳动生产率即存在差异,对于那些劳动生产率增速较低的边缘国家而言,意味着实际汇率升值,国际竞争力被进一步削弱。相反,对于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国家而言,隐形的汇率贬值更加增强了其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若没有有效的财政政策,这种隐性的相对汇率变动容易使得本就存在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扩大化。
根据《马斯特里赫条约》,加入欧元区的标准之一是通货膨胀率不超过3个最低国家平均数的1.5个百分点,且欧洲中央银行以控制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并将目标通货膨胀率设定为接近但不超过2%,但是加入欧元区后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外围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普遍高于核心国家。核心国家在欧元区经济中较高的权重使得欧元区整体通胀率偏低,欧洲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更加符合核心国家的经济发展需求,对于通货膨胀率较高的外围国家而言意味着更低的实际利率。外围国家本可以利用廉价的资金推动其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道德风险的存在使得政府选择了更容易获得短期政治支持的政策,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这种政策上的失误使得大量的资金推高了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造成非贸易部门的非理性繁荣,导致劳动生产率不升反降,从长期损伤了经济增长的根基。
五、简要结论及思考
1.2010-2015年和2016年以来,欧元危机在性质和内涵上具有不同的特征,并综合表现为货币危机、治理结构危机和政治危机。
2009年10月,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引发欧元区银行的支付危机,进而引发欧元汇率剧烈波动。到2010年上半年,欧元危机的说法逐渐流行开来。但什么是欧元危机?其性质是什么?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学术界的见解莫衷一是。通过文献回顾和对欧元本身的分析表明,从内涵和性质上看,与主权国家的货币危机不同,欧元危机具有货币危机、欧元存在性危机和欧元治理框架危机的多种性质和综合特征。特别是对照2009-2015年和2016年欧元危机的表现,可以发现,2016年之前的“欧元危机”更多具有货币危机、债务危机和治理结构危机的性质和特征,2016年以来的欧元危机则更多地表现政治危机和存在性危机的性质和特征。
2.化解欧元危机,仅仅靠解决银行支付问题和治理结构问题还不够,欧元的存在性危机和政治危机,其根源在于单一货币区内成员国的劳动生产率差异。
2016年以来欧元区的政治危机愈演愈烈,化解欧元危机的核心在于缓解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降低贫富差距,使民众的生活水平得以持续改善和提升。要实现这种广泛共享的繁荣仅仅依靠完善欧元区治理框架和结构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建立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基础上的长期经济发展才能切实增强欧元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才能给欧元一个稳定的未来。
首先,对于放弃货币政策工具并且处于相对不利的货币政策环境的国家而言,精心设计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措施是其彻底摆脱经济衰退的唯一出路。各国政府只有摆脱眼前利益的诱惑,着眼于长远制定各项政策,加强技术创新支持,引导资源合理配置,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核心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效益,才能切实缩小与核心国家之间的差距,充分享受货币一体化带来的优势。
其次,各国应加强合作,完善欧元体制机制,增强欧元对不利冲击的风险抵抗力,降低货币一体化对处于竞争劣势国家的不利影响,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供较好的区域环境。
只有在欧元区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差异不断缩小的情况下,各国经济发展才能更加平衡,民粹主义将无立足之地,欧元的前景也将更加明朗。否则,欧元面临的风险将无法从根本上化解。
3.在经济一体化问题上,货币一体化和贸易一体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进程。货币一体化造成的经济冲击更加显著和剧烈,引起的财富分配效应也更加深刻和广阔,因此要求的约束条件也更加严格。
贸易一体化的经济影响是分工深化和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区域经济效应是技术进步和产业转移。相比较而言,货币一体化则主要是可以节约区域内的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的速度和效率。但从动态效应来看,货币一体化将暴露出区域内不同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和竞争力差异,并在缺乏有效调节装置的情况下,加大劳动生产率的分化程度。正像前面所引用的里卡多·赖斯(Ricardo Reis)的信用摩擦模型所证明的那样,由于单一货币区内金融深化的差异,随着金融一体化程度超过金融深化程度,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作用下,非贸易部门的资本回报率将快速上升,贸易部门将因此出现投资下降和萎缩,从而导致非贸易部门以牺牲劳动生产率更高的贸易部门为代价,出现萧条性扩张。该机制的存在意味着,货币一体化要求设立有效的制度装置对此加以调节。在主权货币条件下,一国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可以在统一的国家主权和财政主权条件下得到缓解和解决。但在非主权单一货币条件下,如何解决金融一体化对成员国之间劳动生产率区域分化的影响,欧元区发生的单一货币治理结构危机和欧元存在性危机提供了大量的教训,但答案仍不清晰。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
[1]徐坡岭系新疆财经大学天山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贾春梅系辽宁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作者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2] D. Casimir,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uro area crisis, 《Panoeconomicus》, 2011, 58(5):593-604.
[3] Robert Mundell, Euro is here to stay, Financial Post, June 8,2012
[4] 德国弗伊经济研究所在2017年新年伊始发布预测,认为在未来12个月,意大利超过希腊成为最有可能退出欧元区的国家。——http://ex.cssn.cn/hqxx/tt/201701/t20170104_3368795.shtml[2017-01-05]
[5] Joseph Stiglit, A split euro is the solution for Europe's single currency, Finance Time, August 17,2016
[6] 在维基百科中,目前还没有“欧元危机”(Euro Crisis)的专门词条,搜索Euro Crisis将直接指向European debt crisis(欧债危机)。——https://en.wikipedia.org/wiki/European_debt_crisis[2017-01-05]
[7] 在知网文献检索系统中,以“欧元”和“危机”为关键词,以2009年10月为起点,可以检索到4833条结果,其中95%以上的文献是关于欧债危机的消息、评论或学术论文。以“欧元危机”为关键词,可以检索到253条结果,明确以“欧元危机”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探讨不超过15篇,而明确从货币危机角度研究欧元危机的文献,除了2010年6、7月份的媒体文章之外,严肃的学术讨论几乎没有。在以欧元危机为题的文章中,观点介绍和评论性文章又占很大比重。国内研究欧洲问题的专业期刊《欧洲研究》有1篇在题名中有“欧元危机”的文献(“当福利国家改革与欧元危机不期而遇”,载2013年第1期),有31篇涉及到欧债危机内容的文献。
[8] 2010年2月22日,乔治·索罗斯在《金融时报》撰文谈到欧元的问题时指出“欧元设计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使欧元面临巨大难题”,当时并没有把欧元问题定性为危机。但此后,媒体和欧美的金融机构不断用“欧元危机”来界定当时的欧元区困境,欧元危机的说法逐渐开始流行。国内关于欧元危机的说法也始自媒体和金融从业者,之后被学术界不加区分地转用。参阅:马光远,“欧元危机不会逆转全球经济复苏”,《东方日报》2010年5月11日;郎咸平、孙晋,“欧元危机:渊源与解题”,《银行家》2010年6期,第72-77页;徐杰华,“欧元危机的成因分析及其影响”,《当代经济》2010年7月(下),第79-80页;李长久,“欧元危机的原因和启示”,《红旗文稿》2010年第10期,第14-16页;于冰、武岩,“从‘欧债危机’到‘欧元危机’”,《国际金融》2011年12月,第62-67页;刘昊红,“欧元危机不可能导致欧元终结”,《经济研究参考》2010年第60期(总第2332 期)第36页;
[9] 曹宏苓,“欧元危机与引发机制研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年第6期,第20-33页;弗兰西斯科·吉亚瓦奇,“欧元危机的逻辑”,《国际经济评论》,2012 年第2 期,第52-57页;“The Euro Crisis Faces Three Possible Scenarios”,——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2/08/09-euro-scenarios-elliott[2017-01-05] ;Policy Responses of the ECB in Managing the Euro Crisis and Its Evolutionary Role, ——https://www.kiep.go.kr/eng/publications/pub09_view.jsp?page=1&no=137, 2015.07[2017-01-05]; 彼得·A·霍尔,周艳辉译,“资本主义多样性与欧元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6期,第40-52页。
[10]赵柯:“德国的‘欧元保卫战’:国际货币权力的维护与扩张”,《欧洲研究》,2013年第1期,第64-86页。
[11] 从百度学术对关键词“the Euro Crisis”的检索结果看,2010年以来,应用经济学和政治学科的相关研究达到1.69万篇。这些文献中,以the Euro Crisis为题名,以the Euro Area Crisis、European debt crisis为实际研究对象,或者仅仅以The Euro Crisis为背景探讨其他问题的文献占了绝大部分。
[12] Mr Michael C. Bonello, The Euro: A Crisis of the Currency or a Failure of Politics? Paper from the Colloquium: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the Euro Crisis,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ta, 2 December 2011, ——http://aei.pitt.edu/60629/1/michaelbonellocrisisofthecurrencyupdate2.pdf[2017-01-05]
[13] S. Wood, The euro crisis, 《Policy A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 Ideas》, 2012, 28(2):ED1
[14] Peter A. Hall (2012):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the Euro Crisis, German Politics, 21:4, 355-371
[15] J Frieden,M Copelovitch,S Walte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uro Crisi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16, 49(7):1-30.
[16] Edmond Alphandéry, The Euro Crisis, European Issues No.240 / 14TH MAY 2012
[17] TD. Willett,N. Srisor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uro crisis: Cognitive biases, faulty mental models, and time inconsistency,《Journal of Economics & Business》, 2014, 76:39-54。
[18] A. Heise,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 The Euro Crisis and what went wrong with European Economic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2, 41(2):42-60;
[19] P. Beramendi,D. Stegmueller,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The Eurocrisis, 《Cage Online Working Paper》, 2016; J Frieden,M. Copelovitch,S. Walt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uro Crisi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16, 49(7):1-30.
[20] FV. Perry, W. Gelman, J. Wrieden, IS THERE A WAY OUT OF THE EUR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2013.
[21] Dani Rodrik, Is There a Way Out Of the Euro Crisis? http://www.slideserve.com/lin/is-there-a-way-out-of-the-euro-crisis(June 1, 2013)[2017-01-08]
[22] Susan Christopherson, Gordon L. Clary and John Whiteman,Introduction: the Euro crisis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5 (2015) pp. 843–853
[23] 赵俊杰,“英国脱欧公投留下的话题”,《世界知识》2016年第16期,第47-49页。
[24]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86th Annual Report, Basel,26 June 2016
[25]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PDB_GR[2017-01-14]
[26] http://ec.europa.eu/eurostat/data/database[2017-01-14]
[27]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EO[2017-01-14]
[28]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2011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得出
[29] Paul A.Samuelson Theoretical Notes on Trade Problem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46,No.2,1964; Balassa B. The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Doctrine: A Reapprais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72(6),1964
[30] http://data.worldbank.org[2017-01-16]
[31] http://data.worldbank.org[2017-01-16]
[32] Baumol,W.J.,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7(3),415-26,1967
Fuchs, V.R., The Service Econom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3] http://data.worldbank.org[2017-01-16]
[34] http://data.worldbank.org[2017-01-16]
[35] Maurice Obstfeld and Kenneth Rogoff,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 c1996 Massachusen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200 (chapter 4.1)
[36] http://stats.oecd.org[2017-01-17]
[37] Gamberoni, E., C. Giordano and P. Lopez-Garcia, Capital and Labour (Mis)Allocation in the Euro Area: Stylised Facts and Possible Determinants, ECBWorking Paper Series,2016
[38] Ricardo Reis, The Portuguese Slump and Crash and the Euro Crisis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7/2013a_reis.pdf[2017-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