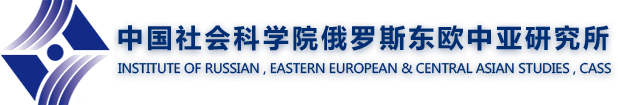[内容提要] 当代俄罗斯国家有能力保持政治稳定,无法实现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这种模式就其本质而言不可持续但却能维持相当长时间。“有稳定无发展”,这就是当代俄罗斯国家治理困境的内涵。本文采用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作为分析框架,试图理解俄罗斯国家治理困境的原因,基本结论是,在俄罗斯,国家与资本结为一体且倾向于长期维持这种现状,社会受到拟制,同时国家也缺乏发展的意愿和能力。这是导致俄罗斯国家治理困境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俄罗斯,展缺失,国家治理,国家,本与社会关系
作为全球性大国俄罗斯,1991年苏联解体获得独立后在较短时期内完成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基本制度的构建。从政治稳定的角度,在1996年以来举行的七次总统大选中,当局推举的候选人都无一例外获得胜利,赢得选举;现任总统普京多年持续享有高支持率。从经济发展的角度,1991独立以来,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经济结构中的能源原材料导向持续强化,社会分化十分严重,属于典型的发展缺失。显而易见,俄罗斯国家有足够能力保持政治稳定,却完全无法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这种模式就其本质而言不可持续但却可以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简言之,政治稳定而经济不发展,这就是当代俄罗斯的国家治理困境的内涵。
一、问题的提出
相关研究表明[1],过去25年俄罗斯发生了一系列积极变化:不再与世隔绝,放弃了命令计划经济和对外贸易垄断,彻底解决了商品和服务短缺,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形成了企业家阶层。总体而言,俄罗斯民众已经完全适应市场经济。
但是,在此期间俄罗斯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仅为1%,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年均通货膨胀率达到54%。投资不增反降,比苏联后期下降10%-15%。生产和出口结构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俄罗斯目前80%的对外贸易依然是燃料和原材料[2]。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程度甚至高于美国。
与此同时,俄罗斯1991年以来总体上的政治稳定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目前情况看,普京政权对俄罗斯政局有着绝对掌控力。在2016年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中,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以下简称“统俄党”)赢得二分之三以上宪法多数席位,进入议会的其他三个政党分别是现政权的卫星党和“体制内反对党”。在2018年总统大选中,参选率67.5%,普京得票率76.69%,创历史新高。在地方层面,统俄党背景的地方行政长官占全部87个联邦主体中的绝大多数。当前,俄罗斯国内并无成气候的反对派,舆论媒体受到严格限制。2014年俄罗斯并入克里米亚后,国内民意空前提振,普京支持率居高不下,处于70 %之上。2018年俄罗斯政府推出的退休制度改革(主要是提高退休年龄)引起广泛社会不满,普京支持率有所下降,但总体上并不会影响政治稳定。因此,可以说俄罗斯总体上保持政治稳定,且这种局面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是可预期的。
那么俄罗斯下一个阶段发展前景如何?
普京总统[3]在2018年3月1日发布的国情咨文中表示,到2025年俄罗斯人均GDP将增加50%(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但经合组织(OECD)2018年初发布的世界经济长期预测[4]显示,若缺乏必要的改革,未来12年俄罗斯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仅增长0.7%,主要限制性因素是劳动生产率(2018-2030年期间将增长0.5%)和人口(劳动人口和就业持续下降)。从长期趋势看,俄罗斯是人均GDP不升反降的唯一的一个OECD国家。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5],俄罗斯26年来经济总体增长了26%,而全球经济平均增长了148%(累计)。2008年-2016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了不足0.2%,低于全球平均增长水平,是“失去的十年”。俄罗斯经济自2009年以来平均年增长率为1%。从俄罗斯官方的预测来看,未来一个时期(2017年起)俄罗斯GDP的年均增长率在2%左右,也低于全球平均增长,也有可能是“失去的十年”。这意味着俄罗斯可以在停滞状态下生活,但俄罗斯经济将持续落后于世界经济,与主要经济体的距离越拉越大。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在1988年发表论文《论经济发展机制》中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拇指法则”,即一个国家的年增长率为g%,那么每过70/g年,它的人均收入就将翻番。[6]据此计算,俄罗斯近25年的年均增长率为1%,若此趋势长期保持下去,意味着俄罗斯人均收入翻番所需的时间为70年!
综上,俄罗斯的发展缺失是一个显著的事实。多年来,俄罗斯政府曾经提出多个十分宏伟的目标,如按人均GDP达到葡萄牙的水平等等,但在经济发展的实际表现却强差人意。一般而言,长期持续的经济发展往往可以理解为国家治理的正面绩效,而发展缺失是国家治理困境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体现。
俄罗斯学者格尔曼[7]在分析俄罗斯国家治理困境(bad governance)时认为,虽然在个别领域(如农业)、个别地区和个别部分(如俄罗斯中央银行)有一些显著的成功案例(история успеха),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治理困境本身。原因在于,在治理质量总体不高的情况下,政治领导人需要一些成功案例向国内外展示政绩。但这些成功案例往往是在人为创造的十分特殊的环境条件下取得的,其实践一般无法被制度化、无法推而广之并产生乘数效应。因此,这些案例进一步证实了治理困境的存在。张慧君[8]认为,俄罗斯在1990年代转型期间经历了一种激进式、突变式制度变革引发的国家整体制度结构协调失灵所产生的系统性危机,属于典型的“治理危机”,并且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仍处在进一步的演化过程中,尚未形成一种稳定而有效的国家治理模式。
二、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一个分析框架[9]
本文采用包含三个变量的分析框架,即国家、资本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对我们在俄罗斯观察到的导致发展缺失、发展缺位和发展赤字的国家治理困境加以探究。
一)为何选择国家、资本和社会作为分析的起点?这主要是因为,在现代条件下,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者关键角色。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国家的职能包括秩序供给和制度供给。制度供给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和保障高效的市场制度环境。国家也是产权制度的垄断供给者。同时,现代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呈现为复杂的社会运动,资本和社会力量的参与是题中应有之义。
如果说,国家和社会是一般论述中较为常见的分析起点,而资本则不然。杨光斌认为,资本作为来自与社会的权力,既不同于国家权力,也不同于社会权利(权力);并且从公权力的角度看待资本权力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比单纯地把资本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更能辨析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10]。
因此,将国家、资本和社会三种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为考察发展问题的自变量,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能给我们提供新的视角。
在分析国家、资本和社会这三个重要的自变量及其关系之时,我们提出一个重要假定,即国家、资本和社会三个自变量在互动过程中都可能表现出“强”、“弱”两种情形。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这里的“强”和“弱”指的是国家、资本与社会三个自变量在互动过程中分别相对于其他两个变量的权力关系。
维斯和霍布森认为,“强”国家是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改革的关键[11]。这个论点既适用于发达国家,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此,所谓的“强”国家,不仅是较强的汲取能力,更重要的是有足够的能力抵御来自资本和社会的压力,保持自主性,即既不被资本也不被社会所“俘获”,能够从社会总体利益出发制定和执行有利于社会多数福利改善的政策。同时国家要有足够的智慧,在一定程度上自我限制,免得侵蚀资本和社会的活动空间,从而限制社会和经济的活力。
我们认为,“弱”国家既有可能是缺乏必要的政治意愿,也有可能是缺乏必要的治理能力,使得国家在面对资本和社会力量的挤压时无法保持“自主性”,无法提出并实现发展议程。
“强”资本是有竞争力的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但同时也可能以垄断和腐败、甚至绑架公权力等方式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是如果资本“弱”,也就是缺乏必要的活动空间,这同样也可能导致经济发展的迟缓和停滞。
社会稳定多数的福利的改善是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结果之一,也应该是国家实现经济发展所追求的社会目标之一。社会权利的保障涉及经济活力与社会活力。白平则认为,强社会是一个自主性强、组织化程度高、社会自我服务能力强、具有创新活力、对国家政治生活参与程度高且影响大,是富裕、和谐、民主的法治社会。[12]
而一个“弱”的社会必然是结构上和价值观体系的高度碎片化和“原子化”,社会成员不得不采取“生存策略”,从而使得整体上无法形成有效的社会压力从而对国家和资本力量产生节制。
总之,政治国家(state)、资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既有控制,更有协调,是持续的互动关系。三者关系的可欲目标是可持续发展【或者是“善治”(Good Governance),即“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三者关系的结果体现为公共政策,体现为一个政治体能否构建出一种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与分配公正的良好秩序[13]。
二)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的逻辑类型
表:国家、资本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类型(+表示“强”;-表示弱)
|
|
国家 |
资本 |
社会 |
|
1 |
+ |
+ |
+ |
|
2 |
+ |
+ |
- |
|
3 |
+ |
- |
- |
|
4 |
+ |
- |
+ |
|
5 |
- |
+ |
+ |
|
6 |
- |
- |
+ |
|
7 |
- |
+ |
- |
|
8 |
- |
- |
- |
上述表格给出的是国家、资本与社会在互动过程中逻辑上可能形成的八种关系。
第一种情形是,国家、资本和社会恪守各自活动的边界,保持良性互动,相互关系和谐。实在而言,这无疑是一种“理想类型”。
第二种情形是国家和资本结为一体,社会受到压制因而缺乏活力,腐败横行,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显而易见,是这种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
在第三种情形里,国家控制一切,资本和社会缺乏相应的活动空间。社会经济活动缺乏活力。在第四种情形里,国家强且社会十分活跃,但缺乏资本。在第五种情形里,国家孱弱,资本强大、社会力量活跃。第六种情形则是国家和资本均缺位,社会力量缺乏制约,整体上呈现出无政府状态。第六种情况是社会力量肥大,国家和资本孱弱甚至缺位。第七种情况则是国家与社会孱弱,资本独大。第八种情况则可以忽略不计。
三)对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之逻辑类型的进一步解释
第一,国家、资本和社会关系呈现为相对和谐的情形往往是特定政治体长期持续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原因。同样地,从本表所呈现的逻辑的角度看,国家、资本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失衡是更为常见的情形。经验事实也支持这一点。例如,琼斯认为(琼斯,2018),世界是由各种形态和规模的经济体组成的。一些经济体增长迅速,一些经济体根本就不增长,大量的经济体——实际上是绝大多数经济体——介于这些极端之间。换言之,国家、资本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发生失衡的情况常有,而能够保持平衡的情况在逻辑上和经验上不常有。
第二,如果从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角度观察全球所有经济体的治理绩效并将其想象为一个连续的光谱的话,光谱的一端的是治理良好,另一端则是所谓“治理失败的国家”,实际上大多数经济体位于光谱的广泛的中间地带,或者更为偏向“治理良好”一端,或者更为偏向治理失败一端。
第三,从实际运作的层面看,国家、资本与社会各自具有完全不同的行为逻辑。国家的行为逻辑是政治和安全,资本是逐利的,而社会则关注分配正义、环境等涉及稳定多数的福利等。同时这三种权力都趋于扩张。
第四,国家所代表的利益与资本和社会的利益并不总是完全契合的或者往往是不相契合,甚至是矛盾的或者冲突的,呈现为复杂的互动关系。我们认为,国家、资本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互补、协调、正和(positive-sum)博弈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如果我们认为这三个自变量之间关系的平衡导致可持续发展这样“善治”的结果话,那么套用经典作家的话来说就是,发达的经济体是相似的(不同程度地作对了许多大体相同的事情),而不发达的经济体各有各的问题(不同程度地做错了许多大体相同的事情从而导致不发展)。
第五,如果我们将长期经济增长和人民福祉改善作为目标来看待国家、资本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话,对于失衡现象要更为“容忍”,在寻找和分析导致失衡的原因时则要更为谨慎:国家、资本和社会都可能分别或者同时出现越位、缺位和错位的情况,而这些情形都可能导致发展缺失。但在关键的发展阶段,尤其在快速增长阶段,尤其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如果是国家发挥主导作用,引导资本和社会进入良性互动关系,则这种失衡甚至可能是引发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必要对国家过渡介入进行调整,国家有必要采取某种程度的“自我限制”,给资本和社会让出一定的活动空间。对于这个调整时机和幅度的把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与此同时,国家、资本与社会之间的“力量对比”失衡且难以调整,实则是导致出现治理难题的根本原因。
第六,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国家、资本与社会三个变量当中,国家因垄断暴力而具有更大的权力。而一旦国家被资本所“俘获”,其权力可能造成的破坏力量十分巨大且难以被抑制。同样道理,垄断暴力的国家变得“孱弱”,则有可能被社会力量取而代之,新的社会革命有可能摧毁旧的国家,从而造成其“发展中断”。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俄国见证了两次类似的情形。
三、俄罗斯的案例
纵观全球,俄罗斯发展缺失的案例并非特例,世界上许多国家和经济体具有类似的情形。与此同时,从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导致俄罗斯发展缺失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国家建构、历史和社会等因素密切相关,而政治性因素无疑是最主要的。
一)俄罗斯国家、资本与社会的建构及其性质
在苏联时期,全能国家(totalism)侵占社会的全部活动空间:国家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社会“寄居于”国家之内[15]。命令计划经济意味着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完全由计划调配,价格仅仅是一个统计单位,因而资本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换言之,既不存在市场[16],也没有资本的容身之地。
俄罗斯独立之后,国家、资本与社会构建的时序是,从全能国家过渡到有限政府;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而大规模私有化的结果是大资本崭露头角。值得说明的是,在俄罗斯,新制度的建立尤其私有化是一个有着强烈政治主导的过程,其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为新制度奠定经济社会基础。与此同时,这个过程伴随着国家从社会领域退出,逐步放弃苏联时期所承担的社会保障,以及社会的“原子化”。新的社会阶层从原来的均质、高度同质化社会结构中开始分化出来。而新的中产阶级出现的同时大多数人从原来的“近似中产阶级”陷入贫困,甚至沦为赤贫。社会结构的分化的同时也就是社会结构和价值观体系的繁缛化。
利亚波夫[17]认为,苏联解体和新制度“植入”的结果不是某种混合体制,而是形成一种所谓的“后苏联资本主义”体制。其根本性特点是,权力和资本相互贯通且高度集中在少数精英手里。事实上,新出现的是一个单一的“权力-资产”制度安排。而“权力”和“资产”的掌管者就是国家官僚。资源(权力和资产)高度集中,政治和社会行为者的数量实际上被减少到最低限度。官僚阶层掌权权力和资产之后,既不愿意与社会分享权力,也不愿意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更不愿意放弃权力(发生更替)。这个特点决定了类似的体制倾向于维持现状。
“权力与资本结为一体”(сращениевластиибизнес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扭曲是显而易见的。其直接的后果就是经济结构调整无法完成,经济现代化进程迟缓,腐败规模巨大,严重影响经济的竞争力和投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造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信任的缺失。
从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来看,俄罗斯国家资本主义、寡头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经济结构的简单化。出口收入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油气行业。天然气行业高度垄断,石油行业则是有限竞争。经济上的寡头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政治领域的竞争。或者说,政治领域不可能是开放竞争式的。开放竞争式的政治体制必将威胁到高度垄断的油气行业。
一般而言,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市场创造,而有能力创造市场的只能是国家。如果“权力与资本结为一体”,意味着在业已建立的市场经济框架之内,国家的角色错位、越位与缺位三者并存。国家不能提供足以激励经济主体开展活动的公共品——市场,那么也就无法希望经济活动产生较大的效益,最终惠及社会大多数人,因而呈现为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社会和谐反过来进一步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对俄罗斯案例的进一步的解释
俄罗斯学者基洪诺娃[18]认为,从社会文化角度看,在俄罗斯,国家被看作是根本性的经济人,要求强化国家的作用、扩大国有资产等,依然是俄罗斯人与西方文化国家的关键区别。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庇护关系(Патрон-клиентскиеотношения)意味着人民授权给国家,赋予其无限制的权力和资产,同时也将责任转移给国家,要求其必须对人们的生活状况和涉及到全国的决策负责。并且,如果国家不能够兑现自己的承诺,那么人民向其提出要求,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回其权力的合法性。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与西方国家有根本性的区别。
与此同时,在俄罗斯,国家的神性不仅是一个社会意识中的幻象(фантом),而且是一种切实的生活经验。自然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等是俄罗斯国有经济部门的基础。而国家则是相当部分居民经济福祉的保障者。在此情况下,对国有部门的任何动作都被政府、政治精英和社会看作是破坏社会稳定。
全能国家的合法性及其在经济生活中的特殊作用显示,国家主义连同其所特有的权力与资产的一体依然是俄罗斯社会意识的规范。经验数据表明,俄罗斯特有的文化模型在最近15年在社会文化现代化的路上走了很远。与此同时,俄罗斯还依然保留着许多属于新国家主义社会的民族文化规范。其中最为典型的特点就是国家在社会生活、经济中的特殊作用,权力与资产的一体。这就使得独立于权力之外的资本和社会力量几乎缺乏“合法”的活动空间。
三)历史因素
历史上,中世纪之后的欧洲国家之间竞争的最高和最后方式表现为战争。在欧洲历史上,战争与国家相互建构。战争催生了民族国家的建设,以及民族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债务发行与偿还能力不断增强。反观俄罗斯。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其财政汲取能力依赖进口关税和国内税收。同时,俄罗斯帝国向欧亚大陆东部【乌拉尔、西伯利亚、远东】和南部【中亚、高加索】的扩张,获得的大量利益【贵重的皮毛贸易】与英国、荷兰等国在海外的掠夺所获不可同日而语。但因为这一切在陆地上发生,而当时的陆路交通十分落后。换言之,与发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相比,俄国沙皇的统治力过于强大。从供给和需求两端都无法催生对机器大生产的需要。虽然俄国身处欧洲,与欧洲列强竞争,甚至一度以“欧洲宪兵”自居,但其硬实力建立在人数众多、装备水平与欧洲相似的军队基础上。换言之,与欧洲国家相比,俄国人不是以商业立国,而是以军力立国。这就决定了其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问题是,这种“路径依赖”持续近三百年。二十一实际的今天,俄国人面临的挑战是全球化。产业发展已经不能归结为机器工厂,而是产业链、生态。换言之,彼得一世、斯大林等“买来的现代化”的故事已经不可能重复。
新制度主义代表人物诺思[19]认为,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有两个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第二个目的将导致一系列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以便降低界定、谈判和实施作为经济交换基础的契约所引起的费用。
换言之,有效的产权组织能够实现社会产出的最大化,甚至可能缴纳更多的赋税供统治者支配。但是,有利于统治者的政治制度却不可能建立在有效的产权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无效的产权组织之上。当有效的产权组织快速发展时,有可能削弱无效的产权组织,从而对统治者的经济基础构成挑战。因此,统治者有可能有意识地保护无效的产权组织而遏止有效的产权组织。而当有效的产权组织发展受到遏制时,整体税收就会减少,因而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就会收到限制。国家不能发展,是统治者和民众双方的损失。
俄罗斯独立二十多年来,经历了特点迥异的两个阶段。叶利钦时期,俄罗斯陷入了转型带来的剧烈动荡之中。国家能力的急剧下降、国家机器的孱弱、国家基本秩序的丧失,是这一时期俄罗斯国家治理的核心困境。为了走出这一困境,普京时期,俄罗斯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国际油价走高的有利条件下,提升了国家能力,加强了国家机器,恢复了国家的基本秩序。但是,在普京执政长达18年后[20],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明显又陷入了新的困境之中。
尤其是近年来,俄罗斯政府从行政程序、政府职能,包括对行政许可、企业注册登记、企业经营活动的检查等角度试图对政商关系进行规范,试图通过立法厘清权利的边界,包括建立企业注册的“一个窗口”等制度减少行政壁垒和寻租空间。从实践角度来看,这些改革和调整所取得效果并不明显。在正式的、法律上明文规定的规则之外,实际上起作用的是大量的非正式制度在调节经济关系。
总之,从国家、资本与社会角度对俄罗斯独立以来的时间所作的考察显示,由于国家与资本结为一体,资本依附与权力,权力与资本相互贯通,因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缺位(姑且称之为“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国家自主性”),是造成发展缺失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在俄罗斯,历史上国家上具有最高价值(表现为国家的“神性”),因此1991年以来俄罗斯社会对国家地位作用的认知和需求虽然在发生变化,但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传统主义的。这更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游离于社会之外的状况,使得国家、资本力量的扩张缺乏外部制约,也使得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的调整缺乏必要的动力,体制不可避免地陷入僵化而无法自拔。由于这种体制能够使得执政集团的利益最大化,执政集团因而倾向于维持现状。因此,俄罗斯无论何人当政,政治上都倾向于继续维持这种体制,而在意识形态上往往用特殊主义、孤立主义的叙事,利用传统主义的社会意识来强化其合法性。因此,这种“有稳定而无发展”的局面究其本质而言不具有可持续性但却可以延续很长一段时期。
四、初步结论
从国家治理质量的角度看,全球范围一些国家治理良好,一些国家治理质量欠佳,而大部分国家介乎于这二者之间。俄罗斯的治理困境【bad governance】是普遍性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俄罗斯的特殊性在于,它有着全球大国的雄心壮志【амбиции】。
当今世界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新的发展模式正在显现,全球力量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嬗变,新的主体正在出现。而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具有结构性和国际化两大特点。所谓结构性就要求社会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做出调整。经济发展实际上成为一种社会运动,普遍参与。而国际化则意味着参与国际市场和国际合作是不可避免、无法回避的。
2000年以来,普京带领俄罗斯走出了叶利钦时期的混乱与失序,实现了国家稳定,但却又使俄罗斯陷入了新的国家治理困境中,即国家目前的稳定建立在外生因素之上,国家陷入了长期性的发展缺失。俄罗斯国家治理面临的困境可以被概括为“有稳定无发展”,即政权可以维持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外生因素之上的稳定,但无力实现国家发展,且这种发展的缺失呈现出长期性的趋势,甚至有被路径锁定的风险。
俄罗斯独立以来的制度建设在形式上已经结束,但尚存深刻矛盾,国家仍处在深刻变革之中。对于当代俄罗斯而言,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国家治理模式。问题是,现有的治理模式与长远的国家利益之间,当局所宣示的成为多极世界一极、全球性大国地位的宏大目标与民众改善福祉的诉求之间存在深刻的冲突和矛盾。从长远角度看,俄罗斯在国家治理问题上面临的两大挑战是,第一,发展的主体从何处来?第二,如何找到合适的政治实践,不是将改革的内容化约为如何在财政开支、私有化和维持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之间保持平衡,而是建立起发展的内生机制。总之,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依然是当下和未来一个时期俄罗斯面临的迫切任务。
[1]2017年11月初,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主题为“1991-2016年俄罗斯经济市场化转轨总结。下一步怎么办?”的学术研讨会。本文引述的观点来自这个研讨会的材料。参见:http://www.ras.ru/news/shownews.aspx?id=20dd5b1f-fe3a-456f-8024-519592234c63
[2]俄罗斯银行(中央银行)一项研究显示,在近年俄罗斯出口的1200中商品当中,只有117种(约占10%)具有比较优势,且大多数是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占出口商品总价值的97%。其余1000多种商品不具有比较优势。因此,俄罗斯出口多元化的潜力十分有限。
资料来源:http://www.vedomosti.ru/economics/articles/2016/06/30/647371-diversifitsirovat-rossiiskii-eksport-poluchaetsya
[3]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6957
[4] https://www.vedomosti.ru/economics/articles/2018/03/07/752952-rossiya-otstanet-ssha
[5]http://www.ras.ru/news/shownews.aspx?id=20dd5b1f-fe3a-456f-8024-519592234c63
[6][美]查尔斯·I·琼斯,迪特里奇·沃尔拉特:《经济增长导论》,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7]Гельман В.Я. Исключение и правила: «история успеха» и «недостойное правление» в России/Владимир Гельман: Препринт М-64/18.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2018. – 38 с.
[8]张慧君:《俄罗斯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治理模式演进》,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版。
[9]本文作者在《欧亚地区的发展缺失:基于国家、资本与关系的分析》一文中首次系统论证了这个分析框架。参见:薛福岐:《欧亚地区的发展缺失:基于国家、资本与关系的分析》,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年第5期。
[10]杨光斌:《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1][澳]琳达·维斯,[澳]约翰·M·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 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版。
[12]白平则:《社会与强国家: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
[13]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4]参见:薛福岐:《欧亚地区的发展缺失:基于国家、资本与关系的分析》,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年第5期。
[15]范思凯:《俄罗斯市场化民主化转型中国家与市场、社会关系研究》,辽宁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
[16]苏联时期十分活跃的“黑市”无论如何都不应当被看作是是现代经济意义上的市场。
[17]ANDREI RIABOV. The Post-Soviet States. A Shortage of Development in a Contex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iversity. RussianPoliticalandLaw, vol. 52, no.2, March-April 2014, pp.30-43
[18]Тихонова Н.Е., Динамика нормативно-ценностной систем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995-2010 годы //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11. № 4. С. 5-19.
[19]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20]我们把梅德韦杰夫任总统的4年也算作普京执政的时期,因为这四年中,梅德韦杰夫基本仍沿着普京时期制定的路线和政策施政,普京本人也仍然在当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