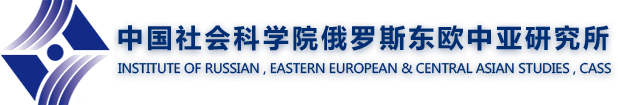【内容提要】外交决策历来是国际政治研究的重点,其中艾利森决策理论以个人性情论和历史情景论为视角,建立了以理性为核心的决策模式,强调人格特质的重要意义。俄罗斯外交决策同样深受总统人格特质的深刻影响。这在普京总统任期尤为明显。普京时代的主旋律是俄罗斯的强国战略。在强国战略的背景下,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精英在对外政策的原则与目标上一致:保持俄罗斯在世界上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国家的地位。普京个人经历让普京有坚定的主权观念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强烈意愿。不仅如此,在强调时间性的历史情景中,外交战略文化赋予俄罗斯地缘空间与精英共识的超时空结合,“俄罗斯是独特的”这种理念总是在适宜的时间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概念体系反复出现,这是俄罗斯民族气质在总统人格特质上的映射。从人格特质与战略文化的视角研究俄罗斯的外交决策,可以看到:俄罗斯观念是俄罗斯在世界政治历史长河的冲击下反应与自主探索的结晶。
【关键词】 俄罗斯外交决策 国家利益 人格特质 战略文化 俄罗斯独特性
【作者简介】 庞大鹏,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一、决策理论与分析路径
外交决策历来是国际政治研究的重点。一般认为,国家利益决定外交决策。分析俄罗斯的外交决策,一个可以借鉴的分析路径是首先概要分析国家利益的内涵,进而揭示俄罗斯的国家利益,随后探讨俄罗斯国家利益与外交决策的互动关系,还可以进一步预测俄罗斯外交的发展趋势。这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经典的研究路径。可以说,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国家利益与外交决策关系上最经典的表述是: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关系到外交政策的本质以及全部政治学说的基本问题。
国际关系理论在范式辩论的过程中逐步完善。时至今日,研究国家利益可资借鉴的路径较为丰富。比如,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注重道德和法律对于国家利益的约束,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注重制度和规范对于国家利益的塑造。当然,最有力的工具还是注重实力和利益分析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这对于当前特朗普执政后美国非自由主义霸权形式的外交举措及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尤其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在研究方法丰富的同时,国家利益的内涵也在不断完善,既包含安全与物质方面的关注,又包含道义与道德方面的关注。
那么,如何确定国家利益呢?要确定国家的利益,必须首先对这个国家的性质有清楚的认识。国家利益取决于国家特性。国家特性又是由哪些方面决定的呢?亨廷顿认为美国的国家特性有两个主要要素:文化与信念。从这两个要素出发,可以分析国家特性,进而确定国家利益,最终审视外交政策。第一个要素主要是指价值观和早先移民的习俗。美国早先移民是北欧人,主要来自英国,信奉基督教,绝大部分是新教徒。这种文化主要包括英语和有关教会与国家关系及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等传统。第二个要素是美国领导人在立国文件中所阐明的一系列普遍的主张与原则: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经济自由主义、有限的政府、私人企业。构成美国特性的这两种成分是密切相关的[1]。
可见,国家特性—国家利益—外交决策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链条。问题在于如何搭建一个分析框架认识一国的国家特性。对于俄罗斯外交的研究也需要从影响俄罗斯国家特性的要素入手,分析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进而研究其外交决策。
关于影响俄罗斯国家特性的要素有哪些,可能见仁见智。本文在评析格雷厄姆·艾利森关于决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从总统人格特质和国家战略文化两个要素出发研究俄罗斯的外交决策。
格雷厄姆·艾利森现为美国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和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他最为世人熟知的是其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其实,艾利森涉猎广泛,他另外一本重要成果《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是在国际关系、公共管理和战略决策等诸多领域中都堪称经典的著作。这部著作通过对古巴导弹危机的案例分析,总结了外交决策本质的三种概念模式,即理性行为体模式、组织行为模式和政府政治模式。在此基础上,艾利森将三种模式进行简化抽象,提炼每种模式的分析单位、概念体系、推导样式及示范性命题,从而使三种模式具有了更广泛的一般意义,不仅可以分析外交政策,还可以对国内行为等问题进行解读。因此,《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一书不仅是国际关系领域的杰出著作,而且是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的经典文献[2]。
笔者对艾利森决策理论有如下评析:
第一,艾利森决策理论产生于国际关系的两极格局时代,但是其理论内涵依然具有适用性。当我们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的既有分析框架时,经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产生于具体时代背景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是否具有穿透历史的解释力。这需要从整个学科发展脉络看具体时代理论范式的适用性。具体到艾利森的决策模式,是与政治学流派的发展变化相一致的,因而依然具有较强的理论适用性。政治学思想流派的演变概括地讲就是从古典主义发展到新古典主义。古典主义政治学最本源的问题就在于政体的运行及管理遵循的是整体主义理念。当发展到行为主义政治学时,其重视的是政体内外的组织行为,观照的是个体主义理念。而当新古典主义政治学以制度为中心重新回归到新制度主义时,体现了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统一性。这与艾利森的决策模式体现的国际关系理论演变过程中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统一对立有异曲同工之处。
第二,“理性”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将不同研究范式直接进行理论简化,区别在于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艾利森本人就将古典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国际制度主义、自由主义、战略战争与理性选择统一起来,进行理论简化,认为国际关系的上述基本理论不存在范式转换,都是由于关于理性假定变化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区别,本质上都属于理性行为体范畴。换句话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演变的过程都是基于理性的硬核,对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不同理解和运用[3]。
第三,在艾利森决策理论的基础上,从层次分析的研究视角看,可以抽象出三种国家类型。艾利森基于对行为主体从简至繁的假定,抽象出了有关行为体信息变化关系的矩阵。在信息最少的“最抽象”的情况下,行为主体是国际体系中一个具有完全理性的“概念化国家”。而当相关细节、信息与背景情况不断增加、越来越具体化,该行为主体就成了某种“类型的国家”,或者是某个“具体的国家”,甚至是处于某个特定时间和空间的某个具体国家。而如果领导人的个人价值与看法对行为体有支配性作用,该行为主体又成为了某种“人格化的国家”。
第四,借用艾利森的一个概念——“移情重构”可以积极探索将外交决策的经典理论模式运用到国际政治研究的区域政治学中,由此加强国别研究的学科性。事实上,正如艾利森指出的,在对政府行为和国际关系的分析与思考中,很多研究人员已经广泛运用了这些概念模式。区别在于有些学者明确认识并运用这些模式,而有些学者还是潜在地使用某个模式的范畴和假定。换句话说,艾利森提出的三种理论模式并不神秘,只是从事国别研究的学者没有在学科自觉规范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模式。
从上述四点评析可以看到,人格化的国家、类型的国家(具体的国家)、概念化国家分别强调了领导人的人格特质对于决策的影响以及国家历史文化对于国家特性的塑造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对应政府政治模式、组织行为模式和理性行为体模式,体现了动态性外交决策有限理性与静态性外交决策完全理性的结合。
具体分析世界政治中的俄罗斯,需要看到俄罗斯的对外行为与国内政治是以一种双向影响的方式相互联系的,这两个领域的问题与组织行为体往往重合,是一种双层博弈。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具有不同的规律,决策者必须做出选择以应对复杂性并决定问题的优先次序。这实际上把俄罗斯视为一个行为协调一致、有目的的个人,这也是大部分从事国别问题研究的学者最常用的分析范式,因为这是理解国家政策选择和行动的特别有效的一个捷径。
在当代俄罗斯,尽管有各种组织行为体的代表人物,但是政府中心区域博弈的人是关注重点。普京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领导者,决策考虑的是外交长远目标,无疑是外交决策博弈的中心人物,因此对于俄罗斯而言,运用政府政治模式解读其外交决策时,主要应关注普京的理念与决策。换言之,从决策理论出发,俄罗斯总统人格特质是解读外交决策的一个重要要素。
本文还想对艾利森决策理论可能存在的一个疏漏提出自己的看法:艾利森决策理论及理论依托的三种分析模式过于关注理性及行为体面临的具体情景。实际上,对于国别研究,或者说对于区域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理解研究对象国的文化。研究俄罗斯问题,用俄国思维理解俄国才能真正实现历史与现实研究的统一。
因此,本文除将总统普京的人格特质作为分析俄罗斯外交决策的一个要素之外,还提出了一个分析要素——战略文化。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政治转型与发展是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国内民主化问题是影响俄罗斯外交的重要因素。俄罗斯在处理同西方的关系,包括俄欧关系和俄美关系中注意从国内民主制度的角度强调俄罗斯对于西方已经没有了敌意。叶利钦和普京都以国内民主制度的变迁与确立努力改善西方对俄罗斯的外交观念,核心是想表明俄罗斯即使具备能力,但是没有了敌意。西方关注俄罗斯是否已经具备了相近的价值观,因此俄罗斯民主化的进程有利于改善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而俄罗斯至今同西方特别是美国不能建立完全信任的外交关系的根本原因恰恰就是西方对俄罗斯国内民主制度及其反映的民主文化的迟疑观望心态。这其实是战略文化在外交决策中的折射。如果对比影响苏联和新俄罗斯外交决策的因素,可以看到两个时期都存在战略文化的影响。苏联时期影响外交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动因的独特结合,这被称为革命—帝国思想复合体[4]。
二、外交决策的现实因素:人格特质
既然人格特质对于外交决策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那么人格特质如何形成?换句话说,人格特质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呢?一般认为,人格特质,包括领导人的信念、价值和态度等,主要突出研究领导人的人生经历,认为这对于领导人的性格特质、理念偏好和价值态度起基础性的塑造作用。人格特质的形成是基于领导人人生关键节点事件与经历综合作用的过程,是个性特点与历史情境互动的结果。俄罗斯著名学者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已经从人格特质的视角论述过俄三位总统叶利钦、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外交政策的不同特点[5]。在卢基扬诺夫看来,首先要分析总统的人格特质,其次要从相反角度看客观现实如何影响总统决策,最后才能综合分析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的关系。三位总统的性格与心理特征迥然不同。通常认为叶利钦是亲西方的自由派,好冲动、刚愎自用;普京是反西方的、咄咄逼人的集权者;梅德韦杰夫具有建设性,但不能独立自主。而上述人格特质又与俄罗斯面临的国际形势和自我国际定位的客观需要紧密相连[6]。卢基扬诺夫展现了俄学者如何从总统个人特质分析总统与外交政策之间关系的研究路径。本文也从这一要素出发做出初步分析,力求从理论层面对俄罗斯外交决策做出分析。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转型与发展已将近30年。当代俄罗斯镶嵌着深深的普京烙印。2014年10月,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会议上,时任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现任国家杜马主席的沃洛金提出“没有普京,就没有俄罗斯” [7]。在此前后,“普京主义”已经成为俄罗斯政治研究的核心词语。
2019年新年伊始,在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经历了2018年地方选举的重大挫折和普京的信任率跌至近年来最低点(35%左右)的政治态势下,“普京主义”再次被执政当局当作俄罗斯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加以宣传。2019年2月11日,普京前八年政治设计的主要操盘手、普京的政治高参、“主权民主”概念的提出者苏尔科夫发表重磅文章《长久的普京之国》,明确表示:“普京主义”代表的理念与制度是百年俄罗斯生存和发展的模式。[8]
“普京主义”所代表的治国理念与制度设计涉及俄罗斯政治、社会、经济、外交、文化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俄罗斯外交决策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普京的人生经历及由此形成的人格特质决定俄罗斯外交决策的特点。从个人性情的内部因素看,从小练习柔道和青年时期担任克格勃特工的职业生涯在塑造和影响普京世界观及其外交决策方面的影响潜移默化,坚韧不拔地维护国家利益始终是普京外交决策的唯一选项。从历史情景论的外部因素看,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普京对此的个人认知让普京逐渐遵从俄罗斯的战略文化与历史传统,形成俄罗斯特色的孤立主义,与形成俄罗斯国家基因的时间与空间因素完美结合。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时代虽然提出过“国家振兴战略”[9],但由于俄罗斯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激进改革,国家治理成效难以令人满意。世纪之交的俄罗斯面临或是继续衰弱或是重建伟大强国的十字路口。也正是由于上述严峻的形势,直接导致叶利钦在第二任期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叶利钦需要将权力转交到一个强有力的、能够服众的接班人手上[10]。
普京在叶利钦的重重考验下脱颖而出。在基里延科和斯捷帕申之后坐上具有接班人意味的总理位子,他立即着手在战略思想领域组织智囊讨论,并形成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献。
普京主张在俄罗斯进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改革,但是强调改革必须从俄罗斯的国情出发,走俄罗斯自己的道路;既反对活跃在俄罗斯政坛上的“共产主义”和“民族爱国主义”,也不赞成“激进自由主义”;既反对回到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也不赞成20世纪90年代导致混乱和危机的自由资本主义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俄罗斯国内外的学者普遍认为,普京走的是“第三条道路”,或称为“中间道路”。关于所谓的“中间道路”问题,从俄罗斯转轨一开始就有争论,叶利钦坚决否认中间道路。1995年8月,叶利钦在评价俄罗斯民主时曾经认为,第三条道路是走向后退的道路,俄罗斯只有走第一条发展道路,即把继续进行的经济改革同发展国家民主结合起来。民主发展的道路在于建立法律秩序、发展保护人权的发达司法制度以及建立中产阶级。1996年2月,俄罗斯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在回答关于在传统的共产主义和向资本主义迈进之间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的问题时就表示,俄罗斯不会在发展道路问题上搞什么发明创造。俄罗斯正在向市场关系、正常而文明的关系体系过渡,既不能盲目模仿法国和德国,也不能模仿美国和日本。如果这样是什么结果也不会有的,俄罗斯有自己的特点。
随着1999年12月《千年之交的俄罗斯》的发表,走所谓“中间道路”一时间成为普京选择何种发展道路的理念标签,而且受当时欧美国家领导人政治口号的影响,俄罗斯国内外认为普京的理念具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然而,正如俄罗斯学者指出的,正因为社会民主思想在俄罗斯土地上实际上无法实现,它们才会显得非常有吸引力。带有俄罗斯特色的社会民主口号从一开始就是乌托邦式的。这不只是因为俄罗斯不存在孕育西方社会民主的类似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存在的恰恰是与此相反的条件,使这种政策从原则上说是不可实现的。社会民主,首先是对建设性工作的市场经济中的收入的调整和再分配。国家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相对稳定的民主机制是这条道路存在的前提。但是,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不存在这样的前提与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普京提出了俄罗斯发展道路的方向,并且将夯实基础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2000年1月13日,普京宣布参加总统竞选。2月25日,俄罗斯《消息报》刊登普京致俄罗斯选民的公开信正式提出了自己的竞选纲领[11]。普京将自己施政的优先方面概括为:“打赢车臣战争”、“加强国家地位”、“打击犯罪”、“消灭贫穷”。这些优先方面在选民中产生热烈反应。2000年3月26日,俄罗斯举行总统大选,普京以52.94%的得票率击败其他10位总统候选人,当选第二任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时代正式开始了。
在“俄罗斯新思想”的基础上,普京不拘泥于“第三条道路”的无谓争论与束缚,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政治举措,鲜明地提出了面向未来的强国战略。在普京第一任期内,强国战略的构想逐渐明晰和完善,并构成普京治国理念的实质内容。普京表示:俄罗斯唯一现实选择是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做一个不反对国际社会,不反对别的强国,而是与其共存的强国[12]。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应当在世界上真正强大的、经济先进的和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俄罗斯的所有决定,所有行动都只服从于这一点。
对外政策即俄罗斯对于国际形势的认识、对自身国际身份的定位以及由此确定的对外关系原则也与强国战略息息相关。强国理念构成了普京时代内政外交的逻辑主线。
普京上述外交决策理念与目标的确立固然有各种影响因素,但是从人格特质的视角看,这是政治领导人从个体行为偏好和价值态度需要以政治理性的外在表现形式将权力投射到政治运动和社会公共事业的过程。普京稳健且进取型的人格特质与他人生经历密切相关。练习柔道和担任克格勃特工的职业生涯在塑造和影响普京外交决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柔道追求实效,练柔道讲究无论形势如何都要成为比赛中最后一个没有被摔倒的选手。这对于普京的外交政策也具有一定含义:不屈服于外部压力。2014年10月,在瓦尔代俱乐部会议上普京表示:“来自外部的压力,就像过去的情况一样,只会使我们的社会得到巩固。” [13]
克格勃的经历则强化了普京的国家主权观念。作为国家强力部门的克格勃,考察培养个人的主要品质是对国家的忠诚和坚韧。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认为,普京有两段重要经历,一是进入莫斯科核心领导层之前他的大部分工作时间是在为克格勃效力,二是在圣彼得堡工作并与经济改革派交往甚密,两种不同的经历被统一了起来[14]。克格勃的经历让普京有坚定的主权观念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强烈意愿。普京坦率地表示:世界上的主权国家屈指可数,只有中国、印度、俄罗斯以及其他几个国家。其余国家都处于一定程度或是非常明显的彼此依赖中,或是听命于集团领导。所以,普京认为,主权是非常珍贵甚至是排他性的东西。俄罗斯不是一个能够在不维护本国主权情况下存在的国家,他要么是个独立主权的国家,要么就根本不存在[15]。2007年2月10日,普京在慕尼黑安全政策问题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对当代世界而言,单极模式不仅不可接受,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实现。现在已经到了以在国际交往各主体利益之间寻求合理平衡为出发点、认真思考全球安全结构的时候了”。2016年席卷全世界的反全球化情绪让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都一筹莫展。普京对此开出的药方是强调必须坚持国家主权原则来“帮助保证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和平与稳定”。普京认为西方大国一贯对全球规则和原则进行不利于俄罗斯的操纵。当规则对西方有利时,西方国家政府就予以坚持,而当规则不符合其切身利益时,那些政府便漠视长期惯例而制定更合心意的规则。坚持主权原则至关重要[16]。2019年2月20日,普京在发表2018年度国情咨文时再次重申,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珍视主权,因为“倘若俄罗斯丧失主权,他就不能成其为国家。一些国家可以,但俄罗斯不行”。[17]
三、外交决策的历史要素:战略文化
在对外关系领域,战略文化是一国历史传统与当代决策的有力结合。战略文化既体现了一国国家性的历史结构因素,也反映了在当代世界政治中一国战略思维要旨所在。就像普京在2019年2月20日国情咨文中简明概括的:“俄罗斯过去是,将来也会是独立自主的国家。这是一条公理。它要么是它现在的样子,要么不存在。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应该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都应该明白和意识到这一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共出台了五份对外政策构想。除了叶利钦时代1993年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总则》,其他四份都在普京时代产生。仔细研读和对比2000年、2008年、2013年和2016年四版对外政策构想,可以看到,尽管文字表述略有差异,但在每份对外政策构想第一部分的对外原则中都体现了普京外交的基本原则:一是俄罗斯要成为强国,二是要着眼周边,三是要警惕外部威胁。
透过外交构想传递出来的原则观念,体现了俄罗斯战略文化的历史一致性。在前述《长久的普京之国》中,苏尔科夫写到:俄罗斯在历史上一共经历过4种主要的国家模式,伊凡三世的国家(即莫斯科和全俄大公国,15—17世纪)、彼得大帝的国家(即俄罗斯帝国,18—19世纪)、列宁的国家(即苏联,20世纪)和普京的国家(即俄罗斯联邦,21世纪)。无论哪种国家模式,他们的内核是一致的,就是说俄罗斯国家性的历史结构因素是一致的。战略文化具有穿越时空的解释力。按照苏尔科夫的概括,俄罗斯战略文化的要点在于拓展性、军事性和人民性。大国意识加强的俄罗斯总把收复所谓的“帝国失地”放在优先地位。俄罗斯前外长科济列夫被公认为亲西方的精英代表,但在1995年也表示为保护国外的同胞,必要的话不惜使用军事力量。科济列夫视野中的“同胞”通俗地讲是“讲俄语的公民”,它不限于俄罗斯国籍的居民和侨居国外的俄罗斯人,即使不同的民族只要平时使用俄语的也包括在内。整个独联体以及拥有很多俄罗斯人的波罗的海三国也都将是俄罗斯的权益范围,而这正是原苏联的版图。这个讲话被认为是俄暴露了恢复“帝国”失地的意图。
叶利钦提倡的“欧洲安全新模式”与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欧洲大厦”主张有很大差别。戈尔巴乔夫是基于北约是欧洲的稳定因素这一认识,甚至允许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在这一点上,戈尔巴乔夫是精英中的一个少数例外。叶利钦的理念是“俄罗斯作为大国应当受到尊敬”,他提出的欧洲安全新模式目的在于为俄罗斯在欧洲问题上发挥影响力打下基础。
梅德韦杰夫是被普遍认为代表新思维的总统,主张与西方建立现代化联盟,但他依然把独联体地区称之为“具有特殊利益的地区”[18],实际上是昔日帝国用语的简化版,依然是势力范围的意思。对于俄罗斯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梅德韦杰夫认为:“我们摆脱了两极模式,这非常好,因为它毕竟阻碍了人类发展。我们曾着重扩大我们的军事潜力,这自然不利于进步。现在所有主要经济玩家、所有主要政治力量、所有主要核武器国家都赞同,世界应当是多极的。俄罗斯联邦也坚持这一立场。我们想成为世界固有的一部分。我们希望能在这个世界占有当之无愧的地位:在经济上、安全领域,占有符合俄罗斯潜力、历史和作用的地位。” [19]
俄罗斯当今的外交政策目标与苏联时期和沙皇俄国时期大为不同。沙皇俄国时期的外交关注欧亚地缘政治,而苏联时期着重推广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到了今天的俄罗斯,战略诉求强烈但能力不如历史上的强盛时期,着眼点依然在对周边的控制上。大国在欧亚地区的竞争促使俄罗斯正视其周围战略环境过去五百年来发生的重要变化[20]。俄罗斯担忧的是在欧亚大陆形成不受俄力量影响的局面。
俄罗斯精英的传统基因在普京身上表现为显性,他就是这一文化的显著代表。俄罗斯的外交传统遵循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要防止出现对俄罗斯安全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威胁的国家和国家集团。第二个原则是,要应对现实存在的挑战构成的主要威胁就必须建立战略纵深体系。战略纵深就是建立一系列持相似立场的伙伴联盟[21]。尤其是第二个原则。这种控制的思想影响到俄罗斯对外部环境的判定。加强对周边地区的控制以求安全的观念就是这样的政治体系和政治理念的一种外在表现。在俄罗斯看来,独联体地区还是应该以俄罗斯为核心联合起来。因为独联体各国仍然存在一些共性问题。这与苏联解体后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联系、实实在在的经济依赖性以及普遍存在的军事安全问题有关。可是,独联体的这种进程越来越受外在的刺激因素——北约和美国的军事目的和计划、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等的影响。独联体范围内的联合也受亲西方领导人的影响。尽管这样,联合的思想对俄罗斯非常有利,这种思想在历史上就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相互融合的核心[22]。
俄罗斯对于俄美关系的判定也受到战略文化的影响。在俄罗斯看来,美国在决定自己对俄罗斯的态度时有几个重要的考虑。第一,着眼于未来。自信的俄罗斯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像在二战中战败的德国和日本那样的盟国,还是再次强大起来的竞争对手?第二,务实。考虑的问题是,俄罗斯帝国解体的时期是否已经结束,或者这个进程在糟糕的治理、社会不公正、无力解决民族问题的情况下仍在继续?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第三个问题:俄罗斯庞大的核潜力及资源将落入谁的手中?[23]更为不利的是,由于俄美的互相影响主要是基于地缘政治,没有受益于欧盟和俄罗斯那样的经济联系,基本上不存在经济上的互相依存关系,因此俄美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常常处于恶化态势[24]。
乌克兰危机后形成的“后克里米亚共识”实际上反映了战略文化在政治进程中的深刻影响。盖达尔早就指出过这一点。他说:“我和我那些在俄罗斯启动改革的同事都明白:向市场经济过渡、俄罗斯适应自己在世界的新地位,这个进程非同寻常。然而我们认为,克服转轨时的退缩、开始经济增长、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这些对自身福利讲求实际的关注会取代恢复帝国的无望幻想。但我们错了。对帝国庄严象征的呼唤是一种操控政治进程的有力手段。” [25]普里马科夫在1996年就任外交部长后就公开批评西方指责俄罗斯在独联体境内用帝国方法建立一体化是不客观的。他认为,俄罗斯寻求独联体地区一体化的客观基础是存在的,而且非常坚实。从地域上看,独联体各国世世代代就是一个统一国家,而不只是在苏联时期。而且在这期间,人员出现大规模移动,人口状况发生根本变化。在俄罗斯境外有2600万俄罗斯人。那里还生活着数千万讲俄语的人,其中包括许多民族在各共和国的代表。这些自然会加深对一体化的向往。普里马科夫还指出,苏联经济一体化程度之高,是世界上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密切的经济联系虽被打破,但人们客观上仍然希望重新恢复。不过,在一体化过程中存在一个限制器,即不能提出重建苏联的任务,这是无法实现的,该提法本身是没有成效的,因为这样我们会破坏同独联体许多国家的关系,阻碍一体化进程。因此,他所领导的外交部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对独联体的工作,目的是要发展一体化进程、支持向心趋势(同时保留独联体所有国家的主权)和消除冲突。
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这种控制周边的思想又经常反过来影响俄罗斯的内部发展,“在俄罗斯的发展过程中,外部影响所起的作用一向比创造性的主动精神更强有力”[26]。对普京来说,他统治的性质和他让俄罗斯恢复“强国”地位的成功是互为条件的。对国内强有力的控制让俄罗斯在海外变得强大;海外的强大为国内的强势统治提供了理由[27]。西方一向擅长分析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问题,经常对从外溢到国际社会的国内制度的内在缺陷和这种外溢产生的国际影响进行研究[28]。在美国看来,俄罗斯表面上的强硬并不单单是愤怒的体现,这反映了一种特殊的世界观。1980年到2000年对于俄罗斯而言是国家实力衰退的时期,俄罗斯先是兵败阿富汗,随后是经济瘫痪直至崩溃。因而,俄罗斯向往赢得尊重、平等。事实上,今日的俄罗斯想赢得尊重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致扭曲了俄罗斯公民和决策者的世界观。不管是在海底插上国旗以宣示对北极的主权,还是把美国人挤出吉尔吉斯斯坦的基地,莫斯科仍把外交当作一场得失所系的角逐。所有这些在美国看来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普京自2000年执政以来,大力恢复俄罗斯的全球影响力并重建他无可争议的地区大国地位。俄罗斯在过去十年制定的几乎每一项重大政策都可以被视作为达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手段[29]。
四、外交决策的本质表征:俄罗斯的独特性
按照苏尔科夫的话来说,俄罗斯不是“深暗国家”,他的一切都在明面上,而且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俄罗斯拥有理解俄罗斯的“深层人民”。俄罗斯的独特性就在于在不同的时代,深层人民可能是农民、无产阶层、无党派人士、公务员等。这样的人也在经历变迁,但是无论何时俄罗斯总是存在这一类人。这一类被称为“深层人民”的群体曾经不止一次在国家遭受入侵时被迫退却,但总能重新回来,而且“深层人民”凭借坚强的整体,形成了无法战胜的战略文化引力,这种引力与俄罗斯的最高领袖的人格特质之间完美契合。这种“俄罗斯的独特性”让人震撼的一点是:俄罗斯在不同时代,社会在变迁,但是俄罗斯的国家性没有变。最高领袖与深层人民之间相互信赖,交流顺畅,这是俄罗斯区别于西方模式的根本所在,是俄罗斯最高领袖人格特质与俄罗斯战略文化的完美结合。俄罗斯社会的内部稳定一直是普京的头等大事。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和90年代的俄罗斯表明,最大的不确定性源自外部环境。从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导致俄罗斯无法偿还债务,到国际恐怖分子组织支持参与车臣战争的反政府派别,再到俄罗斯认为西方插手独联体地区的“颜色革命”,普京确信,在“外部环境中无法控制的环境力量”面前,俄罗斯非常脆弱甚至危险。俄罗斯的“深层人民”对危机源自国外的认知与政治阶层也是高度一致。普京坚信,一个国家只有在能够控制自己命运的基础上,才能为未来制订有意义的计划。他的这种观点与其反复提及并特殊定义的主权民主思想相吻合。对于普京而言,主权意味着能够独立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能让其他人来左右俄罗斯的命运。普京认为,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基本上丧失了主权[30]。
俄罗斯独特性的观念主要是通过与在俄罗斯眼中充满敌意的西方站在对立面得出的。普京欣赏的保守主义哲学家伊利因说:“西方国家不理解,也容不下俄罗斯的身份认同……他们计划把紧紧编在一起的俄罗斯‘扫帚’拆散,再把拆下来的扫帚条一根根折断,最后用它们重新点燃黯淡的西方文明之光。”[31]2013年的瓦尔代会议传递的核心理念就是“没有俄罗斯的世界是不完整的”。普京举1815年维也纳会议和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为例说明只有俄罗斯参与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才能塑造稳定的国际秩序。而一战后的巴黎和会没有俄罗斯的出席,普京认为这次和会上通过的《凡尔赛和约》导致了局势动荡和二战的爆发。普京宣布俄罗斯为一个不可替代的大国。俄罗斯不会谋求“例外论”,但俄罗斯会永远谋求全球命运决策圆桌的一席之地[32]。“对俄罗斯来说,同西方欧洲伙伴保持良好关系非常重要,俄罗斯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俄罗斯已保持着这种关系。但与东方的关系对俄罗斯也非常重要,俄罗斯将同东方伙伴发展经济、政治及其他关系,俄罗斯重视新兴经济地区。因此,俄罗斯将在各个方位开展工作。” [33]
俄罗斯独特论的理念还与俄罗斯民族的超强自信有关。在俄罗斯学者看来,从一系列数据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俄罗斯属于一流国家。俄罗斯这个能源大国不是一种发展构想,而是事实,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占全球能源总出口量的17%。俄罗斯仍是核大国,俄罗斯是资源大国。俄罗斯的原料资源占世界原料资源的30%以上,这不仅使俄罗斯有能力,也向俄罗斯发出严重挑战。历史上从来没有领土面积、资源储量和人口数量如此不成比例的国家。俄罗斯占世界面积的1/8,人口却只占世界人口的2.3%—2.4%。俄罗斯还是政治领导人、政治阶层和各方面专家都有全球思维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可以说,尽管处于危机之中,俄罗斯仍在实行的现代化有利于在社会经济方面也达到符合世界强国的水平[34]。俄罗斯不再是超级大国,但它仍是一个大国。这种地位使俄罗斯有权参与履行智囊职能的机构,管理当今世界各个体系。
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自我意识在苏联解体后的唤醒是一个复杂的长期过程,但只有它能够使国家振兴,能够唤起人民的创造力,使他们团结起来,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规律,俄罗斯历史多次验明了这一点。任何一种伟大的民族思想只要植根于人民都有成功实现的机会,它与政治投机家的政策不同,不图眼前的短期利益。俄罗斯应当自己成长和成熟。俄罗斯不能脱离大国的历史,抛弃丰富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去制造俄罗斯思想。这不是民族自大和傲慢。俄罗斯必须恢复民族自豪感。首先要消除落后和屈辱综合征。国家应当恢复俄罗斯的精神价值,重要的不是小集团的利益,而是国家的最高利益。最重要的是恢复大国思维,俄罗斯大国思维的积淀是对俄罗斯历史命运的思考。大国思维应当成为现实政策和实际行动的原则,证明俄罗斯人民能够团结一致地解决战略性任务[35]。
五、结语
总统人格特质和国家的战略文化深深影响了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俄罗斯精英在对外政策的原则与目标上惊人地一致:保持俄罗斯在世界上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国家的地位。正如原外长普里马科夫所说:“俄罗斯过去是一个大国,现在仍然是一个大国。像任何大国一样,俄罗斯的政策必须是多向和多面的。”“国际局势本身要求俄罗斯不仅是历史上的大国,而且现在也是大国。”这种一致意见认为,虽然承认俄罗斯的能力有限,但是并不认为俄罗斯的有限能力构成俄罗斯在世界上发挥积极作用的障碍[36]。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从人格特质与战略文化的视角分析俄罗斯外交决策,本质上还是研究俄罗斯与世界政治的关系。俄罗斯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领导人人格特质和国家战略文化的形成都是俄罗斯与世界政治在“冲击—反应”的互动中产生的。俄罗斯是世界政治的一部分,世界政治的历史潮流必然对俄罗斯的发展变化产生影响,同时俄罗斯又深刻影响了世界政治的发展变化。这是俄罗斯研究的普遍性问题;但俄罗斯在世界政治历史潮流中或者偏离或者融入,并在这个互动中产生俄罗斯观念,这都是具体时代背景下俄罗斯独特性的体现。这种普遍性与独特性,无疑是俄罗斯研究永恒的话题。
从这种独特性上看,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就是俄罗斯必须面对的问题。俄罗斯传统安全思维一直将邻国看作俄罗斯的安全要义所在。邻国首先是指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认为,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不仅同俄罗斯有特殊的“血缘关系”,而且直接关系到俄罗斯自身的安全。东欧国家向西靠拢,就是这些国家不断疏远俄罗斯的过程。2008年之前,从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来看,它只能是被动地接受这一过程,通过自己有限的外交努力使之对自己的损害降至最低限度而没有其他的政策选择。2008年俄格战争和2014年克里米亚并入,则表明了俄罗斯实施欧亚战略的决心。2014年俄罗斯新版军事学说明确表示:俄罗斯面临的主要外部军事危险是北约东扩。扩大北约军力,赋予北约军队全球性职能,可以让其违反国际法,使北约成员国的军事设施逐步逼近俄联邦国界[37]。建立和扩张破坏全球稳定、损害核弹领域业已形成的实力对比关系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实施“全球打击”构想,太空军事化,发展非核高精度战略武器也是俄罗斯与西方在中东欧地区博弈的焦点。
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认为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大战和大国之间的战争已不可能,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是来自“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恰恰集中在俄罗斯周围。后来随着北约东扩的逼近,俄罗斯又感到对其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西方。在这种情况下,密切同独联体其他成员国的关系,在俄罗斯周围建立“睦邻地带”,就成了俄外交政策“最优先的方面”。与此同时,俄罗斯虽然已从东欧撤出,但仍把这一地区视为自己的“利益范围”,不愿被从这一地区完全挤出,认为双东扩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剥夺和削弱俄罗斯在欧洲传统影响力的过程,强烈反对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归根结底,传统战略思维决定了俄罗斯对世界政治环境性质的判断。在2017年瓦尔代论坛上,普京继2014年的克里米亚回归讲话后,再次发表了关于国际秩序总的看法[38]。在俄罗斯精英看来,西方为了彻底消化冷战的“胜利成果”,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军事安全各个领域把东欧融入西方体系。显然,双方在战略目标上存在结构性的矛盾。
围绕俄罗斯与世界政治之间的关系,冷战结束以来,始终存在两个对立的战略概念,即欧亚大陆体系和欧美大陆体系。主张欧美体系的观点是希望美国通过北约或各种不同的双边和分区条约更紧密地参与欧洲安全事务。欧亚体系的观点则是包括一个重要的布鲁塞尔—莫斯科轴心,围绕这样一个轴心,欧盟会在俄罗斯的密切配合下发挥更大的安全作用。如果说乌克兰危机之前还有个别中东欧国家主张欧亚体系,那么乌克兰危机后欧美大陆体系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地缘政治环境影响深远。
叶利钦时代的主要任务是俄罗斯要留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叶利钦政府不断遭遇危机,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交互出现。叶利钦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新生的俄罗斯政权必须尽快解决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苏联的法律继承问题(也就是俄罗斯在世界上的法律地位问题)、俄罗斯境内外的核武器问题、与邻国建立关系的问题。俄罗斯不可能延续苏联的外交政策,因为苏联在其生存的末期虽然已濒临解体,但仍然是一个超级大国,而且是之一。俄罗斯也难以继承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对于成为国际秩序的支柱也是大国心态而实力不逮。上述局面恰恰构成了叶利钦总统任期内的外交内涵:避免大国地位的彻底丧失,使俄罗斯至少在形式上仍然身处世界主要大国之列。这项任务有三个组成部分:实现国内政治稳定;实现独联体地区稳定;塑造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积极角色。表面上维系国际地位的目标得以实现,但是如何把表面上的大国地位转换成真正的国际实力就成了普京时代面临的问题。
普京时代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历经坎坷:从最初的融入西方,到后来的实力并立,再到现在与西方的相互对立。为了充实维持国际地位的能力,普京整合了内政外交各种资源,这种策略调整是合理的选择。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步步后退,直到2008年8月俄格战争事件,这是后苏联时代终结的标志,后苏联时代的实质是克服苏联解体带来的震荡。由于苏联以和平的方式解体,事实上直到2013年底以来的乌克兰危机都是在消化苏联解体带来的后遗症。这个后遗症特征之一是俄罗斯对20年多年来地缘政治撤退的心理复仇情绪。
结合上述时代背景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俄罗斯传统战略思维与总统个人特质在外交政策上的反映。性格鲜明的叶利钦在执政后期几乎是病夫治国,但却体现了某种不受约束的俄罗斯特质,他的使命是要不惜任何代价让国际社会看到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存在。练习柔道保持警觉并讲求实效的普京恰恰适合完成巩固阵地、夯实国际地位的任务[39]。从这个角度来看,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即便不是前后连贯,至少也是一个整体。两位总统的不同表现正是俄罗斯作为一个国际主体逐渐成长的过程。
总之,从人格特质与战略文化的视角分析俄罗斯外交决策是一个研究俄罗斯与当代世界普遍性与独特性关系的综合性课题,它源于俄罗斯与世界政治的互为影响,作用于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俄罗斯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政治的潮流深深影响了俄罗斯政治的发展,俄罗斯政治的变化又撬动了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形成了俄罗斯独特的观念。
[1]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7.
[2][美]格雷厄姆·艾利森、菲利普·泽利科:《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王伟光、王云萍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3] 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构建》,前言第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4][俄]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康斯坦丁·普列沙科夫:《克里姆林宫秘史》,徐芳夫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376页。
[5] 卢基扬诺夫是俄罗斯全球知名的瓦尔代俱乐部支持与发展基金会研究主任,还是俄罗斯官方主要智库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在俄罗斯官方和学界都有重要影响。
[6]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 Три главы одной истории: 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о как зеркало реальности, http://ria.ru/politics/20110612/386651921.html
[7] Володин: «есть Путин — есть Россия, нет Путина — нет России», 23 октября 2014. http://www.ng.ru/news/483130.html
[8] Владислав Сурков: Долг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утина-О том, что здесь вообще происходит, 11 февраля 2019 года, http://www.ng.ru/ideas/2019-02-11/5_7503_surkov.html?pagen=42&fbclid=IwAR3ct0Nqn3TpMQqnySevtho2Ky25VWB1pYU2yXSaDnB0pxIgFo4JWiR-9SM&id_user=Y
[9]Общими силами - к подъему России.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18 февраля 1998 года.
[10]А.Остапчук, Импичмент перенесен на Осень,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27, 1998 года.
[11]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Открытое письмо избирателям, Известия, 25 февраля 2000 года.
[12]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8 июля 2000 года. http://tours.kremlin.ru/appears/2000/07/08/0000_type63372type63374type82634_28782.shtml.
[13] Kimberly Marten, Putin’s Choices: Explaining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vention in Ukrain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15.
[14] M. K. Albright, Clear on Chechnya,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8, 2000.
[15] Встреча с участникам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14 сентября 2007 года, http://president.kremlin.ru/appears/2007/09/14/2105_type63376type63381type82634_144011.shtml.
[16] Richard Weitz, Russia Wants to Remake Globalization in Its Own Image, November 24th, 2016,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3192-russia-wants-to-remake-globalization-in-its-own-image
[17]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20 февраля 2019 года,http://www.kremlin.ru/events/ president/news/59863
[18] Регионов привилегирован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См.,Тамара Шкель, Пять принципов президента Медведе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1 сентября 2008 года.
[19] Интервью датской радиовещательной корпорации, 26 апреля 2010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transcripts/7559.
[20] Sherman W. Garnett, Russia's Illusory Ambitions,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7.
[21] Никонов Вячеслав Алексеевич,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 новые реальности,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8, Август 2009 года.
[22]Алексей Матвеев, Итог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http://www.ia-centr.ru/expert/7001/.
[23] Викто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ременюк, Приглашение в однополярный мир-США готовятся к переоценке своего внешнего курса,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2 мая 2006г.
[24] Russia Redefines Itself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Washington Quarterly, March, 2007,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publications/index.cfm?fa=print&id=19111
[25] [俄]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王尊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26] [俄]格奥尔基·弗洛罗夫斯基:《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吴安迪、徐凤林、隋淑芬译、张百春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1页。
[27]Robert Kagan, The 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 Why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ill look like the nineteenth, The new republic, 23 April, 2008.
[28] 参见 [澳]约翰·W·伯顿:《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马学印、谭朝洁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9] Owen Matthews, Anna Nemtsova, The World According to Russia-Why, years after the cold war, the Kremlin's still obsessed with getting respect, NEWSWEEK, Sep 7, 2009.
[30] Andrew C. Kuchins and Clifford G. Gaddy Friday, Putin’s Plan: The Future of “Russia Inc.”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February 2008.
[31] Leon Aron, Why Putin Says Russia Is Exceptiona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31, 2014.
[32] Засед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9243
[33]Интервью датской радиовещательной корпорации, 26 апреля 2010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transcripts/7559.
[34]Никонов Вячеслав Алексеевич,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 новые реальности,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8, Август 2009 года.
[35] См. Парламентская газета, 25 октября 2004 года.
[36] Sherman W. Garnett, Russia's Illusory Ambitions,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7.
[37] Военная доктри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Ф 25 декабря 2014 г. N Пр-2976), http://base.garant.ru/70830556/.
[38] Засед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5882
[39]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 Три главы одной истории: 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о как зеркало реальности, http://ria.ru/politics/20110612/3866519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