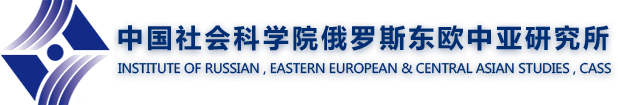马克思恩格斯对摩尔根学说的科学扬弃*
———兼驳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对立论
【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了摩尔根的学说。在对待摩尔根学说方面, 西方学者制造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对立论, 割裂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摩尔根的学说和方法使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私有制的暂时性、完善了唯物史观的“艺术整体”、厘清了氏族在史前社会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扬弃了摩尔根学说的结构、观点和方法, 使之符合唯物主义的要求。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利用摩尔根学说方面存在一些差异, 但他们都高度评价了摩尔根及其学说的革命性。这些差异非但没有构成对立, 反而是一种互补。所谓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并不成立。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 摩尔根学说 科学扬弃 原始社会
作者简介: 袁雷(1987- ), 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北京100048)。
摩尔根是美国著名的民族志学家和历史学家, 是文化人类学进化论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文化人类学主要是比较和研究世界各民族文化、社会的学问, 文化人类学进化学派兴起于19 世纪60年代, 是以进化论学说为基础和方法, 以原始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 关注人类文化的起源和演进问题。1877 年, 摩尔根的科学巨著《古代社会, 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
程研究》(简称《古代社会》) 问世。通过对北美印第安人长达40 年的考察, 摩尔根从他们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解开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史前史(原始社会) 中很多哑谜的钥匙, 并在《古代社会》中首次详细论述了原始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 发现和恢复了成文史的史前基础。《古代社会》是文化人类学进化论研究成果的集大成。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 对之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评述, 在充分借鉴摩尔根研究成果的同时, 科学扬弃了摩尔根学说的结构、观点和研究方法, 发展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目前, 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类学笔记》[1]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简称《起源》) 等著作, 试图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学的研究有一个整体的概括。从总体上看, 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学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尤其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与摩尔根、柯瓦列夫斯基、菲尔、梅恩、拉伯克等文化人类学家的思想渊源关系还没有完全厘清,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 西方学界整体上存着在一种倾向, 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利用和借鉴摩尔根学说以及在对待摩尔根及其学说的评价方面是对立的,制造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对立论, 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为此, 我们力图揭示马克思恩格斯与摩尔根学说的复杂的思想关系, 一方面弥补学界相关研究的不足, 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另一方面积极回应西方学界的错误观点, 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一、西方学者制造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对立的表现
在系统地研读和摘录以摩尔根学说为代表的大量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马克思对史前社会的性质、结构、特点和发展演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创作了包括《摩尔根笔记》在内的《人类学笔记》。马克思原打算利用这些成果, 尤其是关于摩尔根的研究成果, 撰写一部专门论述史前社会的科学巨著。然而, 天不假年, 马克思还没有来得及开展这项工作就与世长辞。
在整理马克思的遗稿时, 恩格斯发现了《摩尔根笔记》, 于1884 年2 月上半月对之进行了详细研究。同年2 月底—3 月初, 恩格斯研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在此过程中, 恩格斯发现摩尔根对北美印第安人和许多古代民族的社会制度的研究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在摩尔根的著作中找到了新的事实证据, 可以证实马克思和他关于史前社会的看法。为了完成马
克思的遗愿, 恩格斯在利用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尤其是《摩尔根笔记》以及其他文化人类学家著作的基础上, 创作了著名的《起源》,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原始社会,尤其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 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关于原始社会的学说。可见, 马克思恩格斯对摩尔根学说的研究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然而, 一些西方学者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待摩尔根学说方面的观点是对立的, 制造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对立论。
对摩尔根学说吸收和借鉴方面的对立。英国学者卡弗指出: “恩格斯放弃了马克思对摩尔根的许多质疑, 并且直接将他的考察重点转向‘结论’, 进而造成似乎是马克思和摩尔根共同支持‘唯物主义观点爷这一事实。” [2]在卡弗看来, 恩格斯放弃了马克思对摩尔根学说的质疑, 而重点考察摩尔根的结论, 有断章取义之嫌。英国学者布洛克指出: “马克思的笔记( 《摩尔根笔记》———引者
注) 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概念上一个截然不同之处是, 就笔记而言, 摩尔根的理论框架被驾驭在马克思的广阔视野之内。而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 我们得出这样的印象, 即书中大量篇幅实际上是恩格斯承袭摩尔根的。这就使恩格斯有可能满腔热忱地分享相当专业性的材料———诸如重要的亲属称谓, 或者澳大利亚土著社会的各种详细材料———这正是马克思曾大量舍弃不用的。” [3]可见, 布洛克认为《起源》借鉴的主要是摩尔根的思想, 而其中相当一部分思想为马克思所批判和舍弃。美国学者莱维特指出: “马克思尽管从总体上确实同意摩尔根的观点, 他在《笔记》( 《人类学笔记》———引者注) 中对待摩尔根的态度也要比对待其他三位进化论者(菲尔、梅恩和拉伯克———引者注) 的态度更温和一些, 但他并没有像恩格斯那样, 将摩尔根视为同路人———‘历史唯物主义者’(这是马克思从未使用过的一个术语)。” [4]同时, 美国学者莱文指出: “恩格斯对氏族制度崩溃的描述不仅和马克思的理解有所不同(虽然他的论著是根据马克思的摘要材料写出来的), 而且也和他没有读过的摩尔根本人的原著精神背离。”[5]
可见, 莱文认为恩格斯在写作《起源》时没有看过《古代社会》原文。显然, 上述观点割裂了《起源》与《人类学笔记》之间的内在继承和发展关系, 制造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对立, 割裂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对摩尔根的态度和评价的对立。莱维特指出, 恩格斯对摩尔根的著作给予了更高的评价, 基本上是全部接受; 马克思虽然总体上同意摩尔根的观点, 但是并非不加批判地接受, 还在一些核心观点上不同意甚至驳斥摩尔根的思想, 尤其不同意将摩尔根视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例如, “马克思在《掖古代社会业一书摘要》的标题的一处评论中, 曾对摩尔根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抨击: ‘对财产的最
早观念(!) ……’这里的惊叹号是马克思所作的唯一评注。”[6]美国学者杜娜耶夫斯卡娅指出, 马克思恩格斯对摩尔根的态度和评价存在很大不同, 不仅体现在数量差别上, 即恩格斯从《摩尔根笔记》中只引用了很少几页, 无法反映马克思的思想全貌, 还体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摩尔根的态度上。“马克思承认摩尔根在关于氏族及其早期平均主义社会的理论方面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但是
他的态度和恩格斯不加批判地为摩尔根叫好毫无共同之处: 恩格斯竟然认为摩尔根‘在美国……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非但不认为摩尔根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 而且拒绝了他的生物学主义和进化主义。”[7]概言之, 恩格斯对摩尔根的态度是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 马克思的态度是在批判基础上的借鉴; 恩格斯对摩尔根的评价很高, 将摩尔根看作同路人, 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马克思则对此持批判态度, 有意识地和摩尔根拉开距离。
总之, 一些西方学者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对待摩尔根的态度和评价方面存在着严重对立, 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回应。
二、摩尔根学说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启发和影响
19 世纪60 年代之前, 由于大量的文化人类学成果还没有出现, 马克思恩格斯对史前社会的认识还很薄弱, 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存在着诸多不完善的地方。“在60 年代开始以前, 根本谈不到家庭史。历史科学在这一方面还是完全处在摩西五经的影响之下。”[8]为了弥补这一薄弱环节,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以摩尔根学说为代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在此过程中, 摩尔根的学说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 摩尔根学说使马克思恩格斯最终论证了私有制的暂时性。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革命者,他们把毕生的精力投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实践中, 其学说也服从和服务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史前社会的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揭示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 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要实现这一理论目标, 单纯研究和论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合理性远远不够, 必须论证共产主义公有制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即最好揭示出人类社会存在过一个没有私有制和阶级的发展阶段。但是, 马克思恩格斯起初并没有意识到私有制和阶级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因而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断定“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9]。但是, 根据摩尔根的大量实证调查得出的科学结论, 史前社会并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使马克思意识到: “社会的瓦解, 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 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这(即更高级的社会制度) 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 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10]显然, 私有制不是永恒的, 原始社会不存在私有制, 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原始公有制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可见, 通过吸收摩尔根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论证了私有制的暂时性。
第二, 摩尔根学说使马克思恩格斯完善了唯物史观的“艺术整体”。唯物史观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 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 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块基石之一。19 世纪70 年代前,马克思系统地研究西欧资本主义社会, 创作了《资本论》这一科学巨著, 证明了唯物史观在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效性。然而, 由于资料的局限,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史前社会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 只是根据一些零星的材料做出一些预测。虽然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一般的规律, 但是正如人体解剖无法代替猴体解剖一样, 对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无法代替对史前社会的研究, 更何况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和史前社会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多差别, 因此, 马克思恩格斯无法确定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能否适用于史前社会。通过研究摩尔根的成果, 他们获取了大量关于史前社会的第一手资料, 为完善唯物史观的“艺术整体”奠定了基础。在《起源》中, 恩格斯指出:“摩尔根在美国, 以他自己的方式, 重新发现了40 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并且以此为指导, 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 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 [11]可见, 摩尔根对史前社会的研究证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适用于史前社会。在研读《古代社会》时, 马克思指出: “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 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 而是由较低级的形式进到较高级的形式。反之, 亲属制度却是被动的; 它把家庭经过一个长久时期所发生的进步记录下来, 并且只有当家庭已经根本变化了的时候, 它才发生根本的变化。[同样, 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以至一般哲学的体系, 都是如此。]” [12]在分析史前社会基本结构时, 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家庭在某种意义上扮演着经济基础的角色, 表明了血缘亲属关系和人自身生产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而亲属制度和政治、宗教、法律等则属于上层建筑范畴, 受前者制约。在《起源》中, 恩格斯引用了马克思的这个观点, 表明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性。可见, 通过对摩尔根的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证明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史前社会的有效性。
第三, 摩尔根学说使马克思恩格斯全面把握了史前社会的结构, 科学厘清了氏族这一史前社会的基本单位。1853 年, 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时指出: “克兰不外是按军队方式组织起来的氏族,同任何氏族一样, 它很少用法律来规定什么, 而是受着各种传统的强烈约束。土地是氏族的财产,在氏族内部, 尽管有血缘关系, 但是等级差别占支配地位, 正像在所有古代亚洲的氏族公社一样。” [13]可见, 马克思已经发现了亚洲氏族公社的存在。但是, 在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之前, 当时的流行看法认为: “氏族被看作是家庭的集合体; 但氏族全体加入胞族, 胞族全体加入部落, 部落全体加入民族, 但家庭不能全体加入氏族, 因为丈夫和妻子必须属于不同的氏族。” [14]受此影响, 在1867 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 马克思指出: “在家庭内部, 随后在氏族内部, 由于
性别和年龄的差别, 也就是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分工。” [15]这时, 马克思也将家庭看作人类社会的基础。
根据摩尔根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科学认识到氏族在原始社会的重要作用, 批判了资产阶级学者格罗特将家庭看作是社会制度基础的错误观点: “格罗特说希腊人的社会制度的基础是oikos即‘户宅、炉灶或家庭’, 这是荒谬的。” [16]在此基础上, 马克思科学地厘清了氏族和家庭的内在关系: “在氏族社会的组织中, 氏族是基本组织, 它既是社会体制的基础, 也是社会体制的单位; 家庭也是一种基本组织, 它比氏族古老。血缘家庭和普那路亚家庭在时间上早于氏族而存在; 但家庭不是{社会制度的} 有机系列中的一个环节。” [17]概言之, 在借鉴摩尔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马克思厘清了史前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是氏族, 而不是家庭。这样, 在科学把握氏族的基本结构的基础上, 马克思恩格斯全面把握了史前社会发展的全貌和辩证图景。
第四, 摩尔根的方法对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类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一, 典型研究是摩尔根在开展田野调查时贯彻始终的方法, 马克思在《摩尔根笔记》中摘录道: “发展的道路应该在制度纯粹的那些地区去研究。波利尼西亚和澳大利亚是研究处于蒙昧状态的社会的最好地区; 南北美洲是研究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和中级阶段的社会状况的最好地区。” [18]显然, 典型分析具有普遍性, 强调要抓住特殊对象的特殊矛盾, 展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二, 实证研究是摩尔根学说形成的基础。通过数十年的实证考察, 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 摩尔根写出了《古代社会》。在《人类学笔记》中, 马克思十分注重实证研究, 强调分析、综合、比较、思辨的总体运用。其三, 历史分期法是摩尔根探讨人类社会发展时运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接受了摩尔根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蒙昧阶段、野蛮阶段和文明阶段的提法。恩格斯指出: “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
尝试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 他所提出的分期法, 在没有大量增加的资料要求作出改变以前, 无疑依旧是有效的。” [19]显然, 恩格斯肯定和采纳了摩尔根的历史分期法。可见, 摩尔根的方法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问题。
总之,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并积极利用摩尔根的学说来丰富和发展自身的理论体系。
三、马克思恩格斯对摩尔根学说的批判和超越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摩尔根学说的吸收和借鉴是建立在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之进行科学批判的基础之上的, 绝非简单照搬照抄。
第一,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扬弃了摩尔根学说的结构。虽然摩尔根的学说闪耀着自发的历史唯物论思想的光芒, 但是他的唯物论思想并不彻底。这充分体现在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结构方面。摩尔根在书的框架结构中经常将某某“观念冶的发展作为标题使用, 认为家庭形式变化和私有制产生的原因是观念的发展。这样, 他就颠倒了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意识之间的关系, 认为是精神决定物质、意识决定存在。在书的结尾, 摩尔根指出: “我们今天极为安全和幸福的条件……都是上帝为从蒙昧人发展到野蛮人、从野蛮人发展到文明人而制订的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20]可见, 摩尔根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看作上帝安排好的一个历史进程, 表明他仍然属于唯心主义阵营。在摘录《古代社会》时, 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将原书的结构“生产技术的发展———政治观念的发展———家庭形式的变化和私有制的产生冶改造为“生产技术的发展———家庭形式的变化到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政治观念的发展”。这里, 马克思纠正了摩尔根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不彻底性, 使之符合唯物史观的要求, 即原始社会建立在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生产的基础之上, 私有制使得氏族制度灭亡, 产生了阶级和国家。在《起源》中, 恩格斯也用马克思修改过的结构来否定摩尔根的结构。可见, 马克思恩格斯对运用自觉的唯物辩证法对摩尔根的结构进行科学的改造, 使之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
第二,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扬弃了摩尔根学说的观点。马克思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纠正了摩尔根的一些错误观点: “一切生物之中, 只有人类可以说达到了绝对控制(?!) 食物生产的地步。人类进步的一切伟大时代, 是跟生存资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21]这里, 马克思从史前社会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实际出发, 在绝对控制之后加了括号, 括号里面是问号和感叹号, 表明他不同意摩尔根的论断。事实上, 直到目前为止, 人类也没有达到绝对控制食物生产的地步, 人自身生产和物质生产的辩证关系远比摩尔根的论述要复杂。同时, 摩尔根没有看到火的技术发明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将之作为较次要的发明来论述。对此, 马克思指出, “在较次要的发明中, 摩尔根除了列举取火钻以外(虽然与此相反: 一切与取火有关的东西都是主要的发明!)”[22]。显然, 马克思从技术的角度将火的发明使用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进而使之更符合唯物史观的要求。
第三,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扬弃了摩尔根学说的研究方法。虽然摩尔根用自己的方法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并以之为指导划分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 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 在当时具有革命性价值, 但是他的研究带有自发的唯物主义倾向。以历史分期法为例,虽然摩尔根从物质生产和技术的角度对人类社会进行分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但是由于没有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指导, 他无法在此基础上提炼和发展出能够反映物质生产的生产结构和经济结构等概念, 从而科学解释原始社会的全貌。这也就是《古代社会》的结构不科学的根本原因。同时,摩尔根将物质生产、政治制度、家族制度和财产制度看作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四个事实, 强调他们在人类从蒙昧社会发展到文明社会的进程中是平行前进的。“各种社会制度, 因与人类的永恒需
要密切相关, 都是从少数原始思想的幼苗发展出来的; 它们也同样成为进步的标志。”[23]可见, 摩尔根没有将物质生产看作政治制度、家族和财产制度的决定性力量, 而是将观念的东西看作与物质的东西并存的决定性力量。这表明摩尔根研究史前社会时坚持的是自发的唯物主义原则, 其所描述的原始社会具有机械性的特征。对此, 恩格斯在充分肯定摩尔根描绘的人类社会发展图景所包含的新特征时指出, “这幅图景跟我们此次遨游终了时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幅图景比较起来, 就会显得暗淡和可怜” [24]。可见, 通过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原始社会的深入研究, 恩格斯克服了摩尔根的机械发展观。在此基础上, 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从物质生产的角度改造了摩尔根的历史分期法: “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 人工产品主要是用做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 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 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 [25]这一思想恰恰来源于马克思的《摩尔根笔记》。这样, 马克思恩格斯就运用科学的唯物辩证法改造了摩尔根的方法。
总之, 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全面扬弃了摩尔根的结构、观点和方法, 使之符合唯物主义的要求。
四、马克思恩格斯对摩尔根学说研究的互补性
在科学扬弃摩尔根学说的结构、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评价了摩尔根学说的意义,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 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第一, 马克思恩格斯利用摩尔根学说态度的一致性。一些西方学者认为, 马克思对摩尔根的学说是有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吸收, 恩格斯对摩尔根的学说是不加批判的全面接受。事实并非如此。恩格斯在1884 年4 月26 日致考茨基的信中指出: “如果只是‘客观地’介绍摩尔根的著作, 对它不作批判的探讨, 不利用新得出的成果, 不同我们的观点和已经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阐述, 那就没有意义了。那对我们的工人不会有什么帮助。” [26]显然, 恩格斯对摩尔根的著作是批判地加以吸收, 并非完全照搬, 是为了对工人阶级有帮助。这充分表明,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类学是为无产阶级的总体解放服务的, 他们研究摩尔根的学说是为了论证唯物史观同样适用于原始社会, 进而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提供理论武器。摩尔根研究原始社会是为了论证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并非用之来推动革命。在这个意义上, 恩格斯研究人类学的目的, 与摩尔根创作《古代社会》存在着本质区别。同时, 在《起源》中, 恩格斯不仅运用了《古代社会》和《摩尔根笔记》中的大量资料,还补充了大量材料。对此, 恩格斯指出: “在关于希腊和罗马历史的章节中, 我没有局限于摩尔根的例证, 而是补充了我所掌握的材料。关于凯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章节, 基本上是属于我的……经济方面的论证, 对摩尔根的目的来说已经很充分了, 对我的目的来说就完全不够, 所以我把它全部重新改写过了。” [27]显然, 《起源》并非仅仅利用了摩尔根的著作, 更不是简单地照搬他的结论。
第二, 马克思恩格斯对摩尔根的评价的互补性。一些西方学者认为, 恩格斯对摩尔根的学说评价过高。事实上, 摩尔根运用全新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将其长达40 年的实证研究所掌握的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融合成一个整体, 撰写了《古代社会》, 代表了当时文化人类学的最高成就, 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不朽著作之一。对此, 恩格斯指出: “摩尔根的伟大功绩, 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 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 [28]这里, 恩格斯对摩尔根的历史功绩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他对史前社会的研究方面, 符合客观事实。同时,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恩格斯将摩尔根看作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而马克思则反对这一观点。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摩尔根本人不是一个坚定的、彻底的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 但是他的学说揭示了史前社会不存在阶级、私有制和国家, 具有鲜明的革命性, 违背了资产阶级学者关于资产阶级社会是永恒的观点, 给了资产阶级以重要一击。因此, 《古代社会》出版后, 遭到了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的同样的待遇。英国“史前史冶科学代表一方面抄袭摩尔根的成果, 另一方面又对之采取缄默抵制的态度, 试图抹杀摩尔根的历史功绩。为此, 在1884 年3 月7 日给拉法格的信中, 恩格斯在谈及摩尔根时指出: “他巧妙地展示出原始社会和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的情景。他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并且在自己著作的末尾对现时代作出了共产主义的结论。” [29]这里, 恩格斯对摩尔根的评价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同样, 在《人类学笔记》中, 在谈到用现代观点来揭示荷马时期军事酋长巴赛
勒斯的权力时, 马克思指出: “欧洲的学者们大都是天生的宫廷奴才, 他们把巴赛勒斯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君主。美国共和主义者摩尔根是反对这一点的。” [30]可见, 摩尔根的思想具有革命性。马克思摘录了摩尔根著作中所具有的共产主义思想, 并强调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在1881 年给查苏利奇复信的初稿中, 马克思借鉴了这一思想:“像一位美国著作家(这位著作家是不可能有革命倾向的嫌疑的, 他的研究工作曾得到华盛顿政府的支持) 所说的, 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爷, 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in asuperior form) 的复活(a revival)’。” [31]可见, 马克思高度评价了摩尔根的思想, 并用之来考察俄国社会发展问题。显然, 在对摩尔根及其学说的评价方面, 马克思与恩格斯并不存在明显的对立。
第三, 马克思恩格斯史前社会研究的互补性。《起源》和《人类学笔记》之间不仅不存在对立,反而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一些西方学者指出, 恩格斯在写作《起源》时, 仅仅参照了马克思的《摩尔根笔记》, 而有意地忽略了《菲尔笔记》《梅恩笔记》和《拉伯克笔记》, 存在着人为肢解《人类学笔记》的情况。事实并非如此。任何理论著作都是要解决特定的问题, 而并非面面俱到地解决所有问题。恩格斯指出, 《起源》“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遗愿。不是别人, 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 [32]。可见, 《起源》是为了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来阐述摩尔根成果的意义, 为了论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适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初阶段。因此, 该书主要参照《摩尔
根笔记》是合理的, 因为只有摩尔根才对原始社会的整个发展历史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柯瓦列夫斯基和菲尔的著作主要论述的是东方社会; 梅恩的著作主要论述的是古代法和国家的产生等问题;拉伯克的著作虽然论述文明的起源问题, 但是里面的观点错误较多, 马克思并未对之进行过多的摘录。因此, 摩尔根的著作和马克思的《摩尔根笔记》为恩格斯创作《起源》提供了主要材料, 这并不存在恩格斯有意忽视其他人类学家著作的情况。因此, 《起源》既不是《人类学笔记》的再版,更不是《古代社会》的翻版, 而是独立的科学著作, 是在科学扬弃《古代社会》的基础上对《人类学笔记》的继承和发展。
当然, 在驳斥西方学者制造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对立论时, 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到他们在利用和对待摩尔根学说方面存在的一些差异。例如,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中的重要批注有480 多条, 恩格斯在《起源》中引用的主要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13 条。可见, 虽然《起源》是在《人类学笔记》的基础上完成的, 但没有涵盖后者的全部思想。对此, 恩格斯指出: “我这本书, 只能稍稍补偿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 [33]当然, 这些差异与西方学者强调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对立论有着本质区别。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 也不可能有两种完全相同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不可能完全一致, 必然存在一些差异。也只有在存在差异的情形下,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才有可能实现互补, 进而彰显其整体性。因此, 在反驳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时, 我们必须承认并高度重视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的一些差异, 并分析其产生的深层原因, 同时要摒弃那种认为存在差异就必然会导致对立的简单思维方式。承认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存在差异, 并非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 反而有利于我们有的放矢地驳斥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 进而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总之, 西方学者在摩尔根学说方面制造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仅仅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只言片语得出的, 其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事实上, 恩格斯是“另一个马克思冶。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摩尔根学说问题上关注点略有不同, 但在精神实质、思想方法和主要理论方面并不存在对立, 而恰恰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参考文献: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冶(17CKS004) 的阶段性成果。
[1]1880 年底-1881 年初, 马克思研究和摘录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 并撰写了许多批语和自己的论点, 以及其他补充材料,形成了著名的《摩尔根笔记》。1879 年秋-1880 年夏, 马克思阅读和摘录了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 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约1880 年夏-1881 年夏, 马克思阅读和摘录了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农村》和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等文化人类学著作。1882 年, 马克思还研究和摘录了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这些笔记构成了著名的《人类学笔记》(又称为《古代社会史笔记》)。
[2]【英】页特雷尔·卡弗: 《马克思与恩格斯: 学术思想关系》, 姜海波、王贵贤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第133 页。
[3]【英】莫里斯·布洛克: 《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 冯利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8 年, 第53 页。
[4]【美】西里尔·莱维特: 《马克思的人类学和进化论问题》, 郑伯范译, 《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5 辑(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译文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年, 第79 页。
[5]【美】诺曼·莱文: 《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的人类学》, 林强译, 《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5 辑(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译文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年, 第53 页。
[6]【美】西里尔·莱维特: 《马克思的人类学和进化论问题》, 郑伯范译, 《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5 辑(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译文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年, 第79 页。
[7]【美】拉·杜娜耶夫斯卡娅: 《马克思的“新人道主义”、“民族学笔记”和妇女解放》, 都梁译,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 卷,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年, 第370 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19 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31 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第398 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15 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第353—354 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第610 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第365 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407 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第499 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第500 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第364 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32 页。
[20]【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古代社会》, 杨东蒓等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年, 第402 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第332 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第379 页。
[23]【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古代社会》, 杨东蒓等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年, 第Ⅱ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38 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38 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516 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16-17 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16 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年, 第127 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第510 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572 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15 页。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15 页。
参考文献:
[1] 冯景源: 《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马克思掖人类学笔记业、掖历史学笔记业研究》,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04 年。
[2] 高崧等编: 《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1 辑(《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论文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年。
[3] 黄凤炎: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4] 鲁越、孙麾、江丹林: 《马克思晚年的创造性探索———“人类学笔记冶研究》,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5] 杜章智: 《国外对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 卷,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
社, 2015 年。
[6] 也美页劳伦斯·克拉德: 《掖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业评介》, 马学林译,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
卷,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年。
[7] 也美页劳伦斯·克拉德: 《作为民族学家的卡尔·马克思》, 周裕昶译,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 卷,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年。
[8] 也苏页伊·利·安德烈耶夫: 《马克思的最后手稿: 历史和现实》, 杜章智译,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 卷,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年。